田原先生的收藏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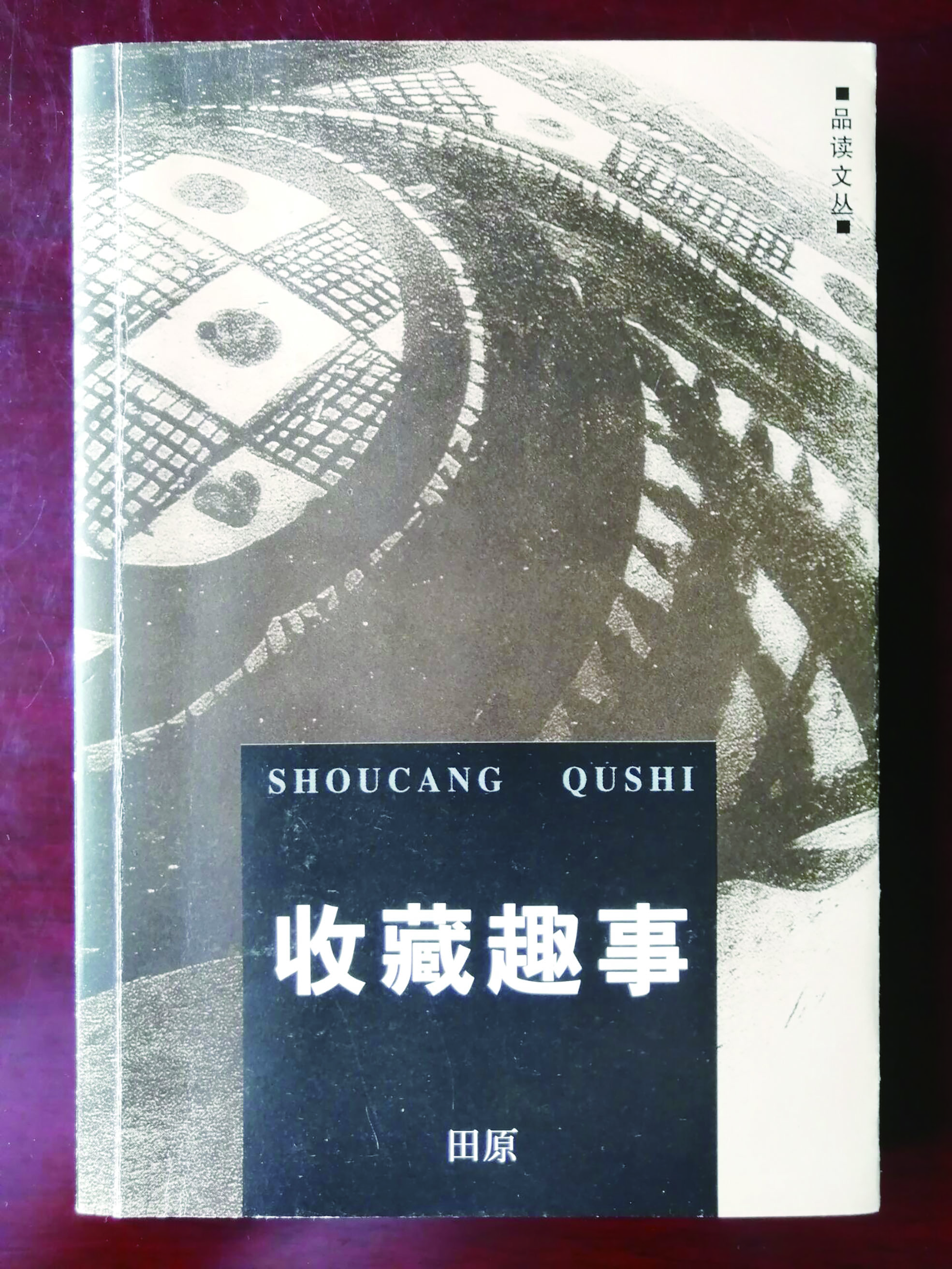
▲《收藏趣事》封面。
马立明
田原先生,1925年生,属于我国老一辈书画家、作家、新闻工作者。他一生著述等身,工作之余,喜收藏。近读他的《收藏趣事》,60件宝贝,60篇短文,“可谓无一物之引证无来历,无一事之追记无根源,令人如读古今史地,如阅民间词典(著名作家俞律‘序’语)。”
如“瓷鸡”一对,为明代物品。此对瓷鸡,背有小孔,呈母鸡孵蛋状,实乃“水注”。水注,是一种专供书画家研墨或调色用的滴水器,属于文房用具之一。母鸡孵蛋,两眼赤红,体温甚高,张嘴喘气,既辛苦又要耐得住寂寞,抚育之爱,确实令人叹服。明代艺人,能用“母爱”这一主题瓷塑成水注,并且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实在令人折服!
田原先生幼年丧母,“未能久得母爱之温存”。当他把玩这对瓷鸡水注时,不禁“情发五中,潸然泪下”,并且“每逢月下独处,终盼先母入我梦来!”田原先生善画,他说他从事国画创作,就是从这对瓷鸡开始,“一笔一画,寄之于情,积累至今,可以信手挥出……”
田原先生有个响亮的笔名:“饭牛”。有人不解,他说:“我出世时在丁丑年正月初五,巧在牛年牛日生。”加之他幼年时为地主放过牛,故而终身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在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他不但写牛,画牛,还特别喜欢收藏各种类型的“牛”艺术品。如汉代陶牛、唐三彩牛、宋瓷牛、明青花牛、清铜牛;民间常见的铁牛、泥牛、纸牛、布牛、紫砂牛、玉石牛、根雕牛、漆器牛、藤编牛、木牛,以及牛领带、牛挂件、牛印章、牛砚台、牛水注、牛面具等。至今,他收集到的各种质地、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公牛母牛,水牛黄牛,老牛小牛,已有100多件。同时,他还在逢牛年时办过几次“牛展”,赢得观众普遍赞许!
在这些众多的“牛”藏品中,田原先生有尊铜牛值得一述:
那是解放初期,他在南京《新华日报》工作,社址在新街口,离长江路极近。长江路虽街道狭窄,旧式平房多,但这里有不少专收废旧报纸、破铜烂铁的旧货店。有次他见一店主货架上有尊铜牛,甚古朴,很想买下。但店主回答:“不卖!”这时他掏出记者证,亮明身份,说自己是藏非倒卖,加上自己属牛爱牛……此时店主终于松了口,说:“你可用铜来换。”田原一听,即飞奔至家,把家里的铜勺、铜锁、铜剪、铜尺集起来,急忙去换。店主一看,觉得此人真还赤诚,于是用秤称了称这些铜件,说:“多了一点。”店主本想找钱给他,田原说:“不用了!”他拿回家,认真清洗,原来是青铜铸的。这尊铜牛,牛背上有个牧童,可作盖取下,原来是件容器。
田原先生还有个轻不示人的“笔筒”。说起这个笔筒,也蛮有趣。
那是他年轻时,去乡下采访。一日傍晚,他正在村头纳凉,此时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小“调皮蛋”。他学着大人的腔调对田原说:“同志,吃过晚饭啦!”田原也认真地搭讪。这样东拉西扯,田原喜收藏的老毛病又犯了。他问这个小调皮,你有什么好东西能拿给我看看吗?小调皮说:“真还有件好东西,前几天被我扔到河里去了。”“真的?为什么丢了?”“那东西对我没用。”田原说:“你能不能捞回来?如捞回来了,我用一打花铅笔和你换!”第二天,这个小调皮真的打捞上来了。一看,原来是个竹笔筒。田原接过笔筒,随即领着他到村头一小店买了一打花铅笔给他。
这个竹笔筒,高不过半尺,口径约寸许,但半圆通身刻的是一幅“山居图”。其“山势起伏,重峦叠翠,如关仝,似范宽。妙在随着刻制的深浅,呈现出山头色彩浓重,逐下渐淡,大有宋画山水皴法。山下有巨松一棵,拔地而起,直矗山头,惜松枝已被不知者刮去,遗憾!下有屋宇三座,筑于水边磊石之上,且有护栏一围。屋有窗,走廊,窗棂刻透,可见内壁,棂条细如发丝,精细之极。廊柱两旁各立一人,仰头舒袖,似在观山,又似在感叹,颇为传神。”你看,这么一个材质普通,但刻艺精湛的笔筒,我看远胜于一般的银笔筒、玉笔筒,难怪田原先生“深置箧中,轻不示人”。
看来,一件宝贝的收藏,有时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田原先生收藏几十年,其藏品上千,可说硕果累累。之后他又能把这些收藏趣事道出来,与人分享,实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