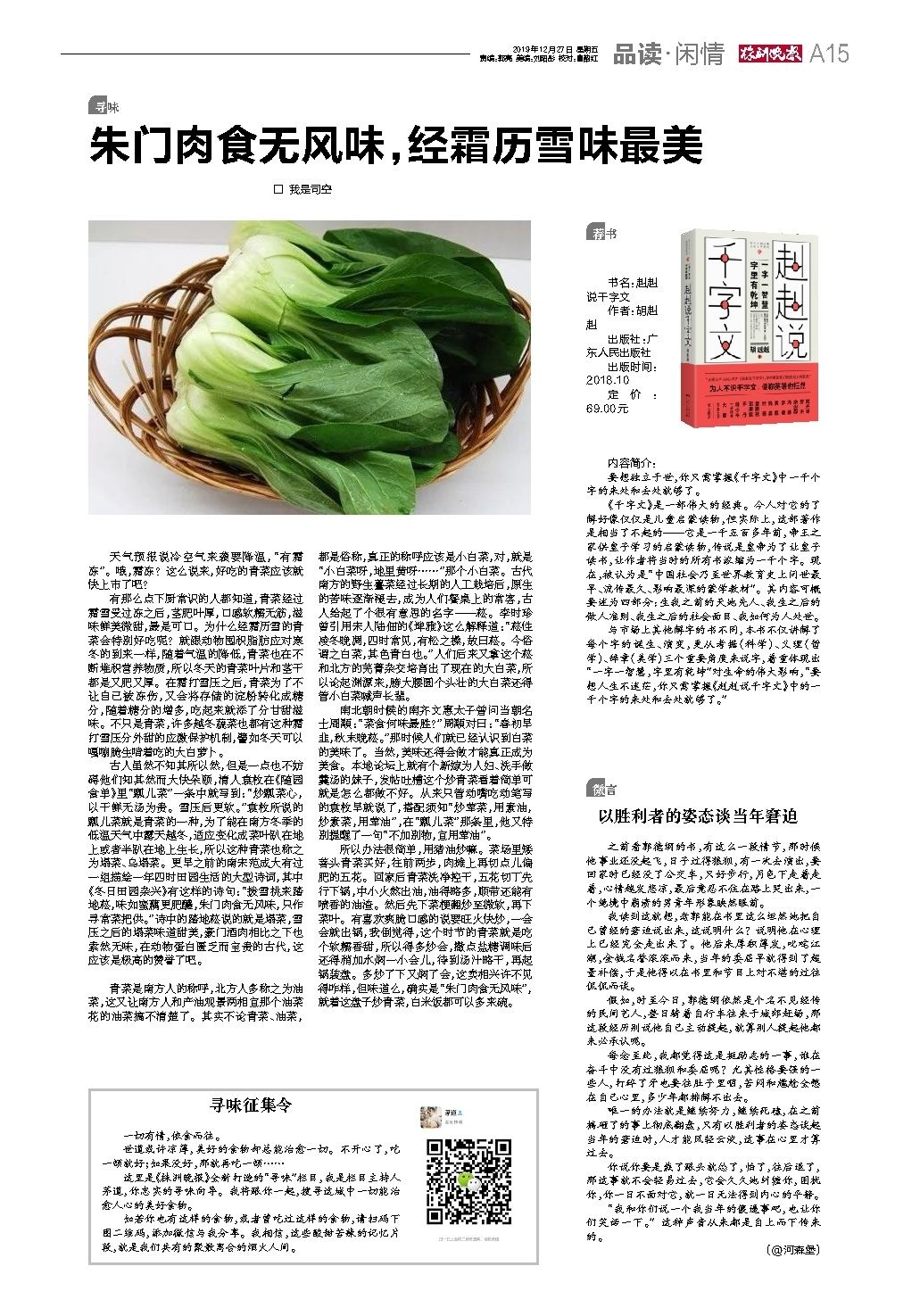朱门肉食无风味,经霜历雪味最美

□ 我是司空
天气预报说冷空气来袭要降温,“有霜冻”。哦,霜冻?这么说来,好吃的青菜应该就快上市了吧?
有那么点下厨常识的人都知道,青菜经过霜雪受过冻之后,茎肥叶厚,口感软糯无筋,滋味鲜美微甜,最是可口。为什么经霜历雪的青菜会特别好吃呢?就跟动物囤积脂肪应对寒冬的到来一样,随着气温的降低,青菜也在不断堆积营养物质,所以冬天的青菜叶片和茎干都是又肥又厚。在霜打雪压之后,青菜为了不让自己被冻伤,又会将存储的淀粉转化成糖分,随着糖分的增多,吃起来就添了分甘甜滋味。不只是青菜,许多越冬蔬菜也都有这种霜打雪压分外甜的应激保护机制,譬如冬天可以嘎嘣脆生啃着吃的大白萝卜。
古人虽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知其然而大快朵颐,清人袁枚在《随园食单》里“瓢儿菜”一条中就写到:“炒瓢菜心,以干鲜无汤为贵。雪压后更软。”袁枚所说的瓢儿菜就是青菜的一种,为了能在南方冬季的低温天气中露天越冬,适应变化成菜叶趴在地上或者半趴在地上生长,所以这种青菜也称之为塌菜、乌塌菜。更早之前的南宋范成大有过一组描绘一年四时田园生活的大型诗词,其中《冬日田园杂兴》有这样的诗句:“拨雪挑来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醲,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诗中的踏地菘说的就是塌菜,雪压之后的塌菜味道甜美,豪门酒肉相比之下也索然无味,在动物蛋白匮乏而宝贵的古代,这应该是极高的赞誉了吧。
青菜是南方人的称呼,北方人多称之为油菜,这又让南方人和产油观景两相宜那个油菜花的油菜搞不清楚了。其实不论青菜、油菜,都是俗称,真正的称呼应该是小白菜,对,就是“小白菜呀,地里黄呀……”那个小白菜。古代南方的野生薹菜经过长期的人工栽培后,原生的苦味逐渐褪去,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古人给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菘。李时珍曾引用宋人陆佃的《埤雅》这么解释道:“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谓之白菜,其色青白也。”人们后来又拿这个菘和北方的芜菁杂交培育出了现在的大白菜,所以论起渊源来,膀大腰圆个头壮的大白菜还得管小白菜喊声长辈。
南北朝时候的南齐文惠太子曾问当朝名士周顒:“菜食何味最胜?”周顒对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那时候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白菜的美味了。当然,美味还得会做才能真正成为美食。本地论坛上就有个新嫁为人妇、洗手做羹汤的妹子,发帖吐槽这个炒青菜看着简单可就是怎么都做不好。从来只管动嘴吃动笔写的袁枚早就说了,搭配须知“炒荤菜,用素油,炒素菜,用荤油”,在“瓢儿菜”那条里,他又特别提醒了一句“不加别物,宜用荤油”。
所以办法很简单,用猪油炒嘛。菜场里矮菩头青菜买好,往前两步,肉摊上再切点儿偏肥的五花。回家后青菜洗净控干,五花切丁先行下锅,中小火熬出油,油得略多,顺带还能有喷香的油渣。然后先下菜梗翻炒至微软,再下菜叶。有喜欢爽脆口感的说要旺火快炒,一会会就出锅,我倒觉得,这个时节的青菜就是吃个软糯香甜,所以得多炒会,撒点盐糖调味后还得稍加水焖一小会儿,待到汤汁略干,再起锅装盘。多炒了下又焖了会,这卖相兴许不见得咋样,但味道么,确实是“朱门肉食无风味”,就着这盘子炒青菜,白米饭都可以多来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