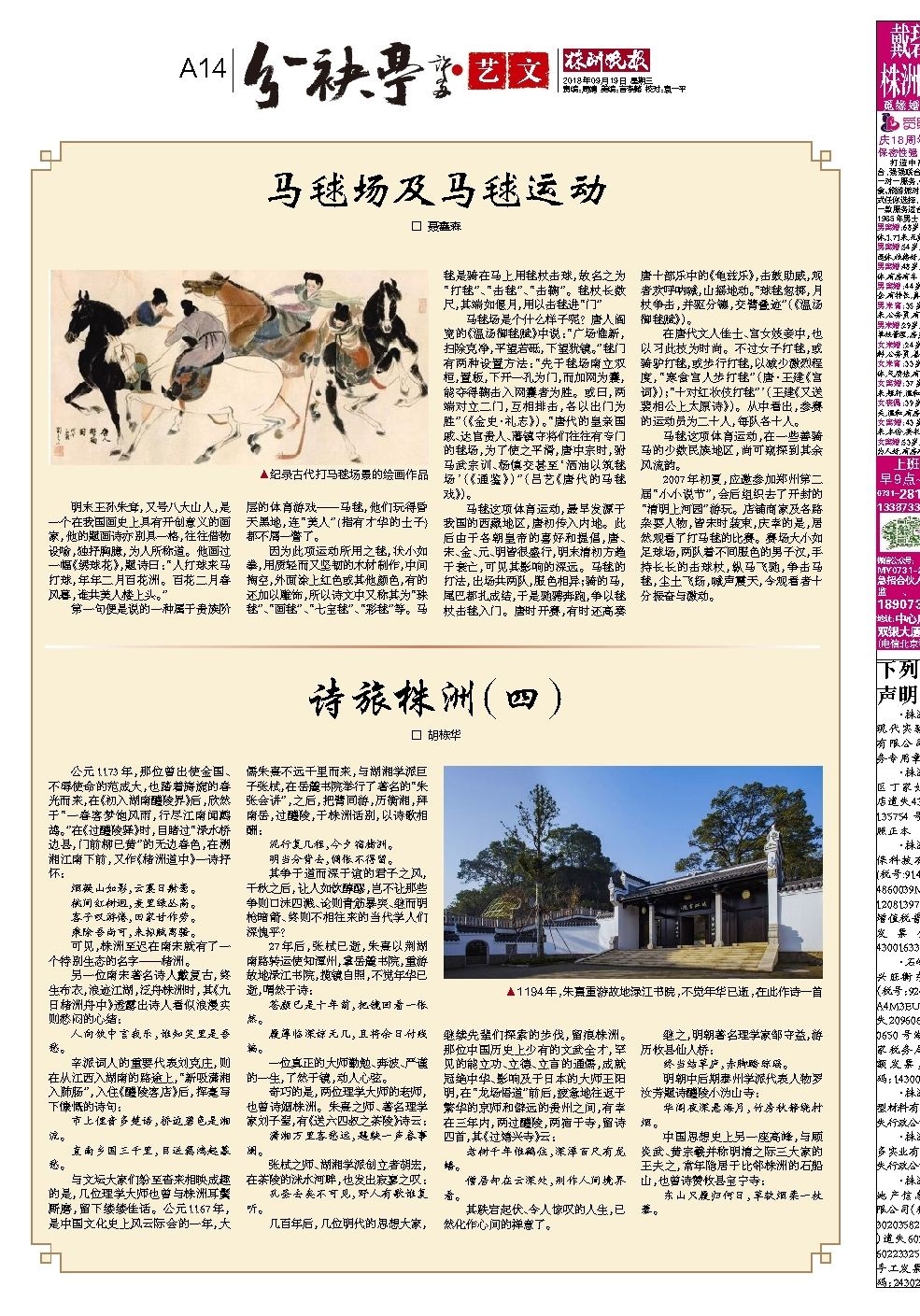诗旅株洲(四)

□ 胡栋华
公元1173年,那位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的范成大,也踏着旖旎的春光而来,在《初入湖南醴陵界》后,欣然于“一春客梦饱风雨,行尽江南闻鹧鸪。”在《过醴陵驿》时,目睹过“渌水桥边县,门前柳已黄”的无边春色,在溯湘江南下前,又作《楮洲道中》一诗抒怀:
烟凝山如影,云褰日射毫。
桃间红树迥,麦里绿丛高。
客子叹游倦,田家甘作劳。
乘除吾尚可,未拟赋离骚。
可见,株洲至迟在南宋就有了一个特别生态的名字——楮洲。
另一位南宋著名诗人戴复古,终生布衣,浪迹江湖,泛舟株洲时,其《九日楮洲舟中》透露出诗人看似浪漫实则愁闷的心绪:
人向饮中言我乐,谁知笑里是吾愁。
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刘克庄,则在从江西入湖南的路途上,“新吸潇湘入肺肠”,入住《醴陵客店》后,挥毫写下慷慨的诗句:
市上俚音多楚语,桥边碧色是湘流。
直南乡国三千里,目送羁鸿起暮愁。
与文坛大家们纷至沓来相映成趣的是,几位理学大师也曾与株洲耳鬓厮磨,留下缕缕佳话。公元1167年,是中国文化史上风云际会的一年,大儒朱熹不远千里而来,与湖湘学派巨子张栻,在岳麓书院举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之后,把臂同游,历衡湘,拜南岳,过醴陵,于株洲话别,以诗歌相酬:
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楮洲。
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
其争于道而深于谊的君子之风,千秋之后,让人如饮醇醪,岂不让那些争则口沫四溅、论则青筋暴突、继而明枪暗箭、终则不相往来的当代学人们深愧乎?
27年后,张栻已逝,朱熹以荆湖南路转运使知潭州,掌岳麓书院,重游故地渌江书院,揽镜自照,不觉年华已逝,喟然于诗:
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
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一位真正的大师勤勉、奔波、严谨的一生,了然于镜,动人心弦。
奇巧的是,两位理学大师的老师,也曾诗姻株洲。朱熹之师、著名理学家刘子翚,有《送六四叔之茶陵》诗云:
潇湘万里客愁远,鶗鴃一声春事阑。
张栻之师、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宏,在茶陵的洣水河畔,也发出寂寥之叹:
孔圣去矣不可见,野人有歌谁复听。
几百年后,几位明代的思想大家,继续先辈们探索的步伐,留痕株洲。那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全才,罕见的能立功、立德、立言的通儒,成就冠绝中华、影响及于日本的大师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后,疲惫地往返于繁华的京师和僻远的贵州之间,有幸在三年内,两过醴陵,两宿于寺,留诗四首,其《过靖兴寺》云:
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
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其跌宕起伏、令人惊叹的人生,已然化作心间的禅意了。
继之,明朝著名理学家邹守益,游历攸县仙人桥:
终当结草庐,赤脚踏琼瑶。
明朝中后期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题诗醴陵小沩山寺:
华阁夜深悬海月,竹房秋静绕村烟。
中国思想史上另一座高峰,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的王夫之,常年隐居于比邻株洲的石船山,也曾诗赞攸县宝宁寺:
东山只履归何日,草软烟柔一杖藜。
▲1194年,朱熹重游故地渌江书院,不觉年华已逝,在此作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