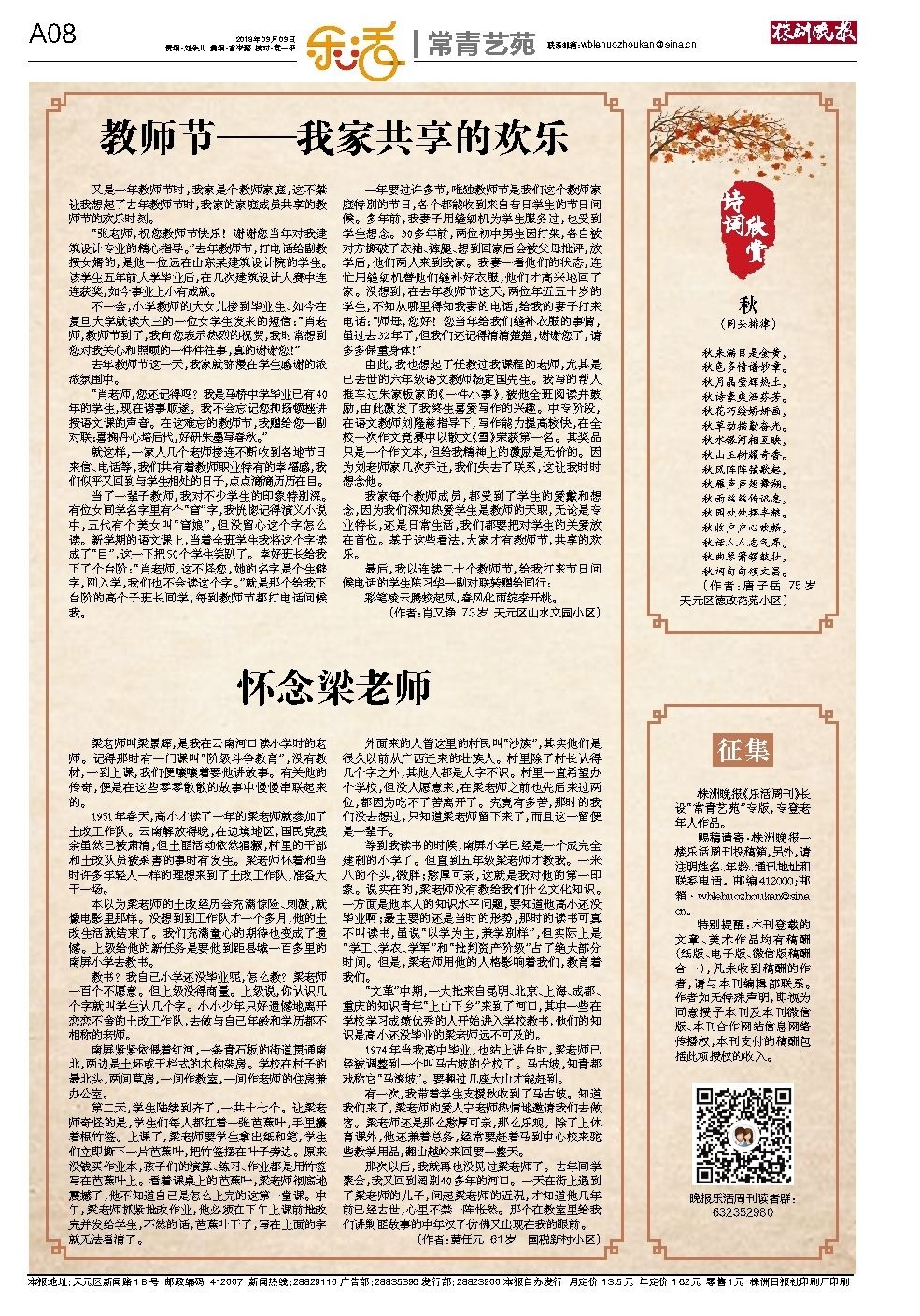怀念梁老师
梁老师叫梁景辉,是我在云南河口读小学时的老师。记得那时有一门课叫“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教材,一到上课,我们便嚷嚷着要他讲故事。有关他的传奇,便是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故事中慢慢串联起来的。
1951年春天,高小才读了一年的梁老师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云南解放得晚,在边境地区,国民党残余虽然已被肃清,但土匪活动依然猖獗,村里的干部和土改队员被杀害的事时有发生。梁老师怀着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的理想来到了土改工作队,准备大干一场。
本以为梁老师的土改经历会充满惊险、刺激,就像电影里那样。没想到到工作队才一个多月,他的土改生活就结束了。我们充满童心的期待也变成了遗憾。上级给他的新任务是要他到距县城一百多里的南屏小学去教书。
教书?我自己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教?梁老师一百个不愿意。但上级没得商量。上级说,你认识几个字就叫学生认几个字。小小少年只好遗憾地离开恋恋不舍的土改工作队,去做与自己年龄和学历都不相称的老师。
南屏紧紧依偎着红河,一条青石板的街道贯通南北,两边是土坯或干栏式的木构架房。学校在村子的最北头,两间草房,一间作教室,一间作老师的住房兼办公室。
第二天,学生陆续到齐了,一共十七个。让梁老师奇怪的是,学生们每人都扛着一张芭蕉叶,手里攥着根竹签。上课了,梁老师要学生拿出纸和笔,学生们立即撕下一片芭蕉叶,把竹签摆在叶子旁边。原来没钱买作业本,孩子们的演算、练习、作业都是用竹签写在芭蕉叶上。看着课桌上的芭蕉叶,梁老师彻底地震撼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完的这第一堂课。中午,梁老师抓紧批改作业,他必须在下午上课前批改完并发给学生,不然的话,芭蕉叶干了,写在上面的字就无法看清了。
外面来的人管这里的村民叫“沙族”,其实他们是很久以前从广西迁来的壮族人。村里除了村长认得几个字之外,其他人都是大字不识。村里一直希望办个学校,但没人愿意来,在梁老师之前也先后来过两位,都因为吃不了苦离开了。究竟有多苦,那时的我们没去想过,只知道梁老师留下来了,而且这一留便是一辈子。
等到我读书的时候,南屏小学已经是一个成完全建制的小学了。但直到五年级梁老师才教我。一米八的个头,微胖;憨厚可亲,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说实在的,梁老师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文化知识。一方面是他本人的知识水平问题,要知道他高小还没毕业啊;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形势,那时的读书可真不叫读书,虽说“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但实际上是“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占了绝大部分时间。但是,梁老师用他的人格影响着我们,教育着我们。
“文革”中期,一大批来自昆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河口,其中一些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开始进入学校教书,他们的知识是高小还没毕业的梁老师远不可及的。
1974年当我高中毕业,也站上讲台时,梁老师已经被调整到一个叫马古坡的分校了。马古坡,知青都戏称它“马滚坡”。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赶到。
有一次,我带着学生支援秋收到了马古坡。知道我们来了,梁老师的爱人宁老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做客。梁老师还是那么憨厚可亲,那么乐观。除了上体育课外,他还兼着总务,经常要赶着马到中心校来驼些教学用品,翻山越岭来回要一整天。
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梁老师了。去年同学聚会,我又回到阔别40多年的河口。一天在街上遇到了梁老师的儿子,问起梁老师的近况,才知道他几年前已经去世,心里不禁一阵怅然。那个在教室里给我们讲剿匪故事的中年汉子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黄任元 61岁 国税新村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