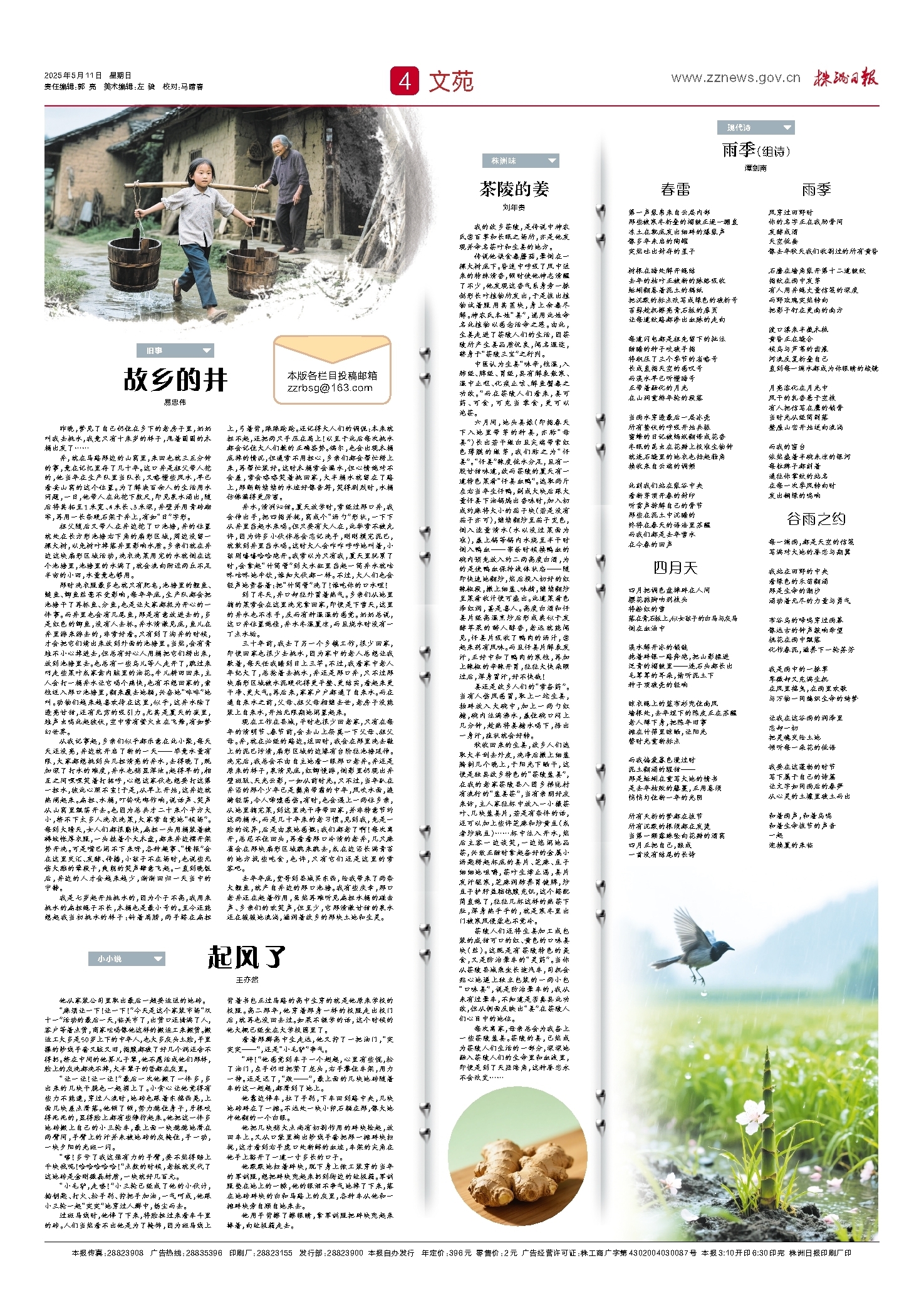故乡的井
易忠伟
昨晚,梦见了自己仍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奶奶叫我去挑水,我竟只有十来岁的样子,甩着圆圆的木桶出发了……
井,就在马路那边的山窝里,来回也就三五分钟的事,竟在记忆里存了几十年。这口井是祖父带人挖的,他当年在生产队里当队长,又略懂些风水,早已看妥山窝的这个位置。为了解决百余人的生活用水问题,一日,他带人在此挖下数尺,即见泉水涌出,随后将其拓至1米宽、4米长、3米深,井壁并用青砖砌牢,再用一长条硬石架于井上,有如“日”字形。
祖父随后又带人在井边挖了口池塘,井的位置就处在长方形池塘右下角的扇形区域,周边没留一棵大树,以免树叶掉落井里影响水质。乡亲们就在井边这块扇形区域活动,洗衣洗菜用完的水就倒在这个池塘里,池塘里的水满了,就会流向附近两丘不足半亩的小田,水量竟也够用。
那时洗衣服最多也就只有肥皂,池塘里的鲤鱼、鲢鱼、鲫鱼丝毫不受影响,每年年底,生产队都会把池塘干了再抓鱼、分鱼,也是让大家都极为开心的一件事。而井里也会有几尾鱼,那是有意放进去的,多是红色的鲫鱼,没有人去抓。井水清澈见底,鱼儿在井里游来游去的,非常好看。只有到了淘井的时候,才会把它们请出来放到外面的池塘里。当然,会有青蛙不小心掉进去,但总有好心人用桶把它们捞出来,放到池塘里去。也总有一些鸟儿等人走开了,跳过来叼走些菜叶或家禽内脏里的油花。牛儿耕田回来,主人会打一桶井水让它喝个痛快,也有不想回家的,索性迈入那口池塘里,翻来覆去地躺,兴奋地“哞哞”地叫。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待在这里,似乎,这井水除了透亮甘甜,还有无穷的吸引力。尤其是夏天的夜里,蛙声虫鸣此起彼伏,空中常有萤火虫在飞舞,有如梦幻世界。
从我记事起,乡亲们似乎都乐意在此小聚,每天天还没亮,井边就开启了新的一天——毕竟水量有限,大家都想挑到头几担清亮的井水,去得晚了,既加深了打水的难度,井水也稍显浑浊。起得早的,相互之间嘿嘿笑着打招呼,心想这家伙也想要打这第一担水,彼此心照不宣!于是,从早上开始,这井边就热闹起来。扁担、水桶,叮铃咣啷作响,说话声、笑声从山窝里飘荡开去。也因为总共才二十来个平方大小,挤不下太多人洗衣洗菜,大家常自觉地“候场”。每到大晴天,女人们都很勤快,扁担一头用桶装着被褥蚊帐厚衣服,一头挂着个大木盘,都来井边摆开架势开洗。可是嘴巴闲不下来呀,各种趣事、“情报”会在这里交汇、发酵、传播,小孩子不在场时,也说些无伤大雅的荤段子,爽朗的笑声肆意飞起。一直到晚饭后,井边的人才会越来越少,渐渐回归一天当中的宁静。
我是七岁起开始挑水的,因为个子不高,我用来挑水的扁担绳子不长,木桶也是最小号的。至今还能想起我当初挑水的样子:斜着肩膀,两手搭在扁担上,弓着背,踉踉跄跄。还记得大人们的调侃:本来就担不起,还把两只手压在肩上!以至于此后每次挑水都会记住大人们教的正确姿势。偶尔,也会出现木桶底掉的情况,但通常不用担心,乡亲们都会帮忙捞上来,再帮忙装好。这时木桶常会漏水,但心情绝对不会差,常会咯咯笑着挑回家,大半桶水就留在了路上,那断断续续的水迹好像音符,笑得剧烈时,水桶仿佛漏得更厉害。
井水,清冽沁甜。夏天放学时,常经过那口井,我会伸出手,把四指并拢,窝成个“汤勺”形状,一下下从井里舀起水来喝。但只要有大人在,此举常不被允许,因为许多小伙伴总会忘记洗手,刚刚摸完泥巴,就敢到井里舀水喝。这时大人会咋咋呼呼地叫着,小孩则嘻嘻哈哈跑开。我常以为只有我,夏天里玩累了时,会拿起“竹筒管”到大水缸里舀起一筒井水就咕咚咕咚地牛饮,谁知大伙都一样。不过,大人们也会轻声地责备着:把“竹筒管”洗了!谁吃你的口水哩!
到了冬天,井口却往外冒着热气。乡亲们从地里摘的菜常会在这里洗完拿回家,即便是下雪天,这里的井水也不冻手,反而有种温温的感觉。奶奶总说,这口井位置绝佳,井水冬温夏凉,而且烧水时没有一丁点水垢。
三十年前,我去了另一个乡镇工作,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很少去挑水,因为家中的老人总想让我歇着,每天任我睡到日上三竿。不过,我看家中老人年纪大了,总抢着去挑水,井还是那口井,只不过那块扇形区域被水泥硬化得更平整、更结实,看起来更干净、更大气。再后来,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而在通自来水之前,父母、祖父母相继去世,老房子没能装上自来水,开始无限期地闲置起来。
现在工作在县城,平时也很少回老家,只有在每年的清明节、春节前,会去山上祭奠一下父母、祖父母。井,就在必经的路边。返回时,我会在那里洗去鞋上的泥巴污渍,扇形区域的边缘有台阶往池塘延伸。洗完后,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那口老井。井还是原来的样子,泉清见底,红鲫慢游,倒影里仍现出井壁斑驳、天光云影,一如从前时光。只不过,当年趴在井沿的那个少年已是鬓角带霜的中年,风吹水面,涟漪轻荡,令人唏嘘感伤。有时,也会遇上一两位乡亲,从地里摘完菜,到这里洗干净带回家,并非特意节约这两桶水,而是几十年来的老习惯。见到我,先是一脸的诧异,后是由衷地感慨:我们都老了啊!每次离开,总忍不住回头,再看看那口冷清的老井,几只麻雀会在那块扇形区域跳来跳去,或在边沿长满青苔的地方找些吃食,也许,只有它们还是这里的常客吧。
去年年底,堂哥到县城买东西,给我带来了两条大鲤鱼,就产自井边的那口池塘。我有些庆幸,那口老井还在起着作用,虽然再难听见扁担水桶的碰击声、乡亲们的欢笑声,但至少,它那清澈甘甜的泉水还在缓缓地流淌,滋润着故乡的那块土地和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