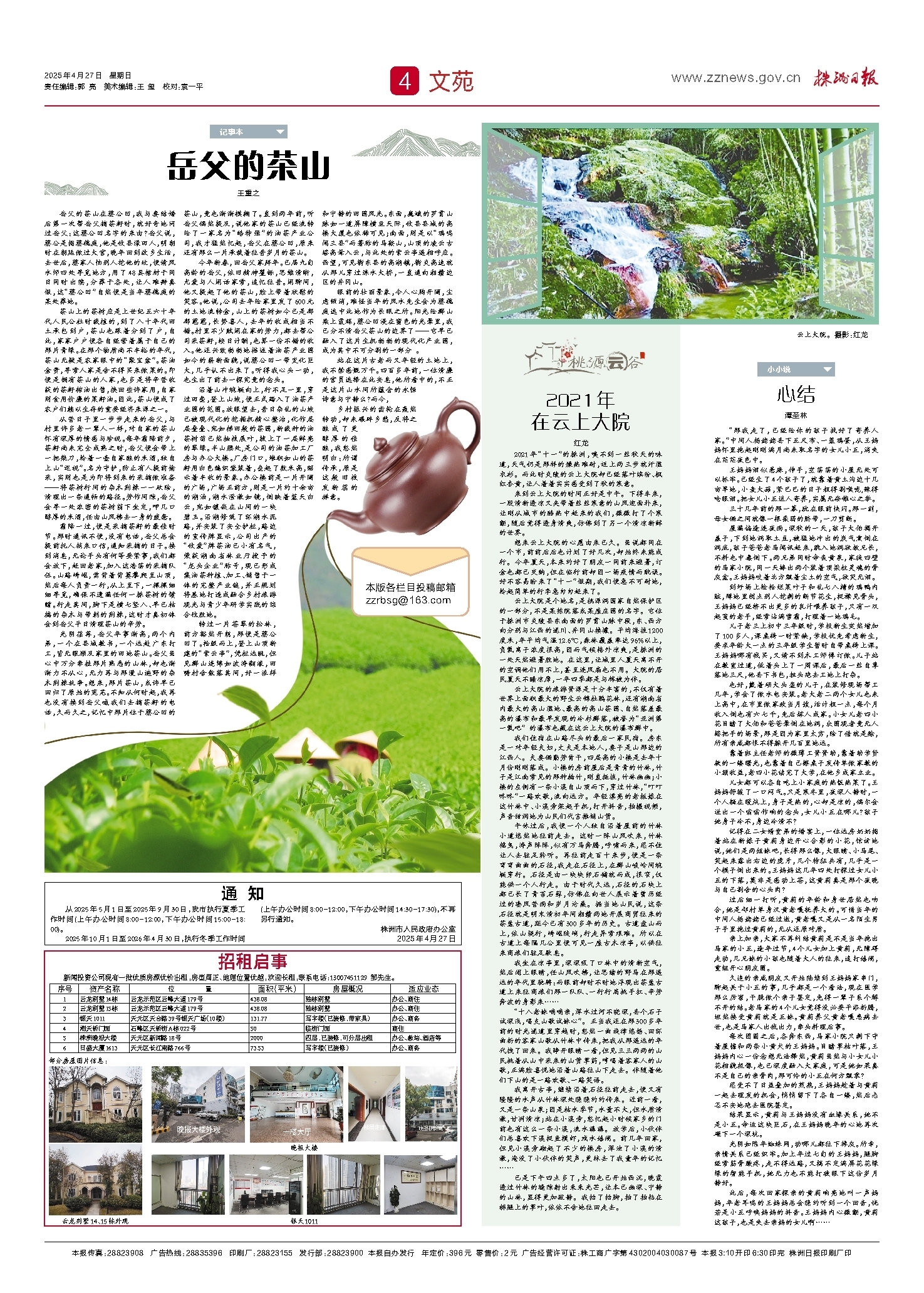心结
谭圣林
“那我走了,已经给你的孩子找好了寄养人家。”中间人杨姥姥丢下五尺布、一篮鸡蛋,从王妈妈怀里抱起刚刚满月尚未取名字的女儿小五,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王妈妈泪似悬麻,伸手,空荡荡的小屋无处可以抓牢。已经生了4个孩子了,就靠着黄土沟边十几亩旱地,小麦大蒜,紧巴巴的日子粗得割喉咙,辣得呛眼泪。把女儿小五送人寄养,实属无奈锥心之举。
三十几年前的那一幕,犹在眼前快闪。那一刻,母女俩之间就像一根柔弱的脐带,一刀剪断。
屋漏偏逢连夜雨。深秋的一天,孩子大伯揭开盖子,下到地洞取土豆,被猛地冲出的炭气熏倒在洞底,孩子爸爸老马闻讯赶来,跳入地洞欲救兄长,不料也中毒倒下。两兄弟同时命丧黄泉,家徒四壁的马家小院,同一天捧出两个装着顶梁柱灵魂的骨灰盒。王妈妈咬着北方飘着尘土的空气,欲哭无泪。
到圩场上捡拾烂菜叶子和乱七八糟的鸡鸭内脏,蹲地里刨点别人挖剩的断节花生,捉襟见骨头,王妈妈已经挤不出更多的乳汁喂养孩子,只有一双起茧的老手,经常沾满雪霜,打理着一地鸡毛。
儿子老三上初中三年级时,学校新生突然增加了100多人,课桌椅一时紧缺,学校优先考虑新生,要求年龄大一点的三年级学生暂时自带桌椅上课。王妈妈哪有钱买,又请不到木工师傅订做。儿子站在教室过道,低着头上了一周课后,最后一丝自尊落地三尺,他丢下书包,扭头跑去工地上打杂。
也好,戴着硕大头盔的儿子,在装修现场帮工几年,学会了做水电安装。老大老二两个女儿也未上高中,在市里做家政当月嫂,活计粗一点,每个月收入倒也有六七千,先后嫁人成家。小女儿老四小花目睹了大伯和爸爸晕倒在地洞,众围观者竟无人搭把手的场景,那是因为家里太穷,除了借就是赊,所有亲戚都恨不得躲开几百里地远。
靠着班主任老师的微薄工资资助,靠着助学贷款的一缕曙光,也靠着自己擦桌子发传单做家教的小额收益,老四小花读完了大学,在他乡成家立业。
儿女都可以各自吃上小家庭的热饭热菜了。王妈妈舒缓了一口闷气。只是寒冬里,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躺在暖炕上,身子是热的,心却是凉的,偶尔会迸出一个嗡嗡作响的念头,女儿小五在哪儿?孩子她身子冷不,身边冷清不?
记得在二女婿堂弟的婚宴上,一位远房奶奶指着站在新娘子黄莉身边开心合影的小花,惊讶地说,她们是两姐妹吧,长得那么像,大眼睛、小马尾、笑起来露出右边的虎牙,几个特征共有,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王妈妈这几年四处打探过女儿小五的下落,莫非是感动上苍,这黄莉真是那个夜晚与自己割舍的心头肉?
过后细一打听,黄莉的年龄和身世居然也吻合,她是邻村单身汉黄老嘎抚养大的。可惜当年的中间人杨姥姥已经过逝,黄老嘎又是从一名陌生男子手里抱过黄莉的,无从还原对质。
亲上加亲,大家不再纠结黄莉是不是当年抱出马家的小五,逢年过节,4个儿女加上黄莉,无障碍走动,几兄妹的小孩也随着大人的往来,追打嬉闹,重组开心朋友圈。
久违的亲戚朋友又开始陆续到王妈妈家串门,聊起关于小五的事,几乎都是一个看法,现在医学那么厉害,干脆做个亲子鉴定,免得一辈子系个解不开的结。老马家的4个儿女觉得没必要平添折腾,坦然接受黄莉就是五妹。黄莉养父黄老嘎患病去世,也是马家人出钱出力,牵头料理后事。
每次团圆之后,各奔东西,马家小院只剩下守着屋檐和两条小黄犬的王妈妈。目睹草枯叶落,王妈妈内心一份念想无法释然,黄莉虽然与小女儿小花相貌极像,也已深度融入大家庭,可是她如果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那可怜的小五在何方飘零?
忍受不了日益叠加的煎熬,王妈妈趁着与黄莉一起去理发的机会,悄悄留下了各自一缕,然后忐忑不安地跑去医院鉴定。
结果显示,黄莉与王妈妈没有血缘关系,她不是小五。命运这块巨石,在王妈妈晚年的心地再次砸下一个深坑。
光阴如陈年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掉灰。所幸,亲情关系已经织牢。加上年过七旬的王妈妈,腿脚经常筋骨酸疼,走不得远路,又搞不定满屏花花绿绿的智能手机,她无力也不能打破眼下这份岁月静好。
此后,每次回家探亲的黄莉响亮地叫一声妈妈,年老耳鸣的王妈妈总会隐约听到一个回音,恍若是小五呼唤妈妈的抖音。王妈妈内心微颤,黄莉这孩子,也是失去亲妈的女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