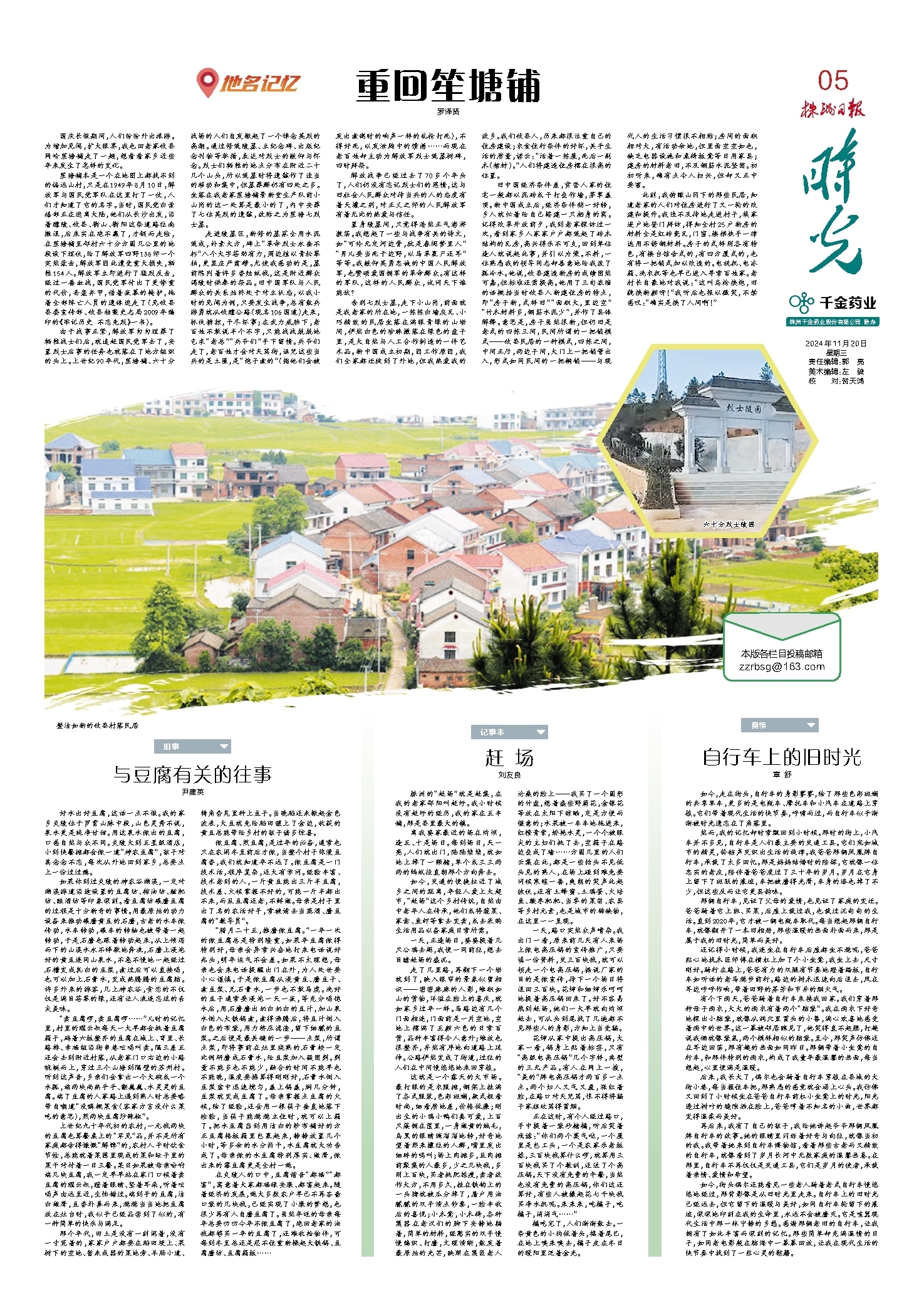与豆腐有关的往事
尹建英
好水出好豆腐,这话一点不假。我的家乡炎陵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山色灵秀不说,泉水更是纯净甘甜。用这泉水做出的豆腐,口感自然与众不同。炎陵大到五星级酒店,小到快餐摊都会做一道“神农豆腐”,孩子对其念念不忘,每次从外地回到家乡,总要点上一份过过瘾。
如果你到过炎陵的神农谷溯溪,一定对溯溪游道沿途设置的豆腐坊、榨油坊、糍粑坊、酿酒坊等印象深刻。看豆腐坊碾磨豆腐的过程是十分新奇的事情。用最原始的动力设备来推动碾磨黄豆的石磨,古老的水车做传动,水车转动,碾车的转轴也被带着一起转动,于是石磨也跟着转动起来。从上倾泻而下的山溪水永不停歇地奔流,石磨上浸泡好的黄豆连同山泉水,不急不慢地一起经过石槽变成乳白的豆浆,煮过后可以直接喝,也可以加上石膏水,变成热腾腾的豆腐脑。许多外来的游客,几上神农谷,贪恋的不仅仅是满目苍翠的绿,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舌尖美味。
“卖豆腐啰,卖豆腐啰……”儿时的记忆里,村里的耀云叔每天一大早都会挑着豆腐箱子,码着六板整齐的豆腐在城上、弯里、长路排、幸福组沿街串巷吆喝叫卖。隔三差五还会去到附近村落,从老家门口右边的小路蜿蜒而上,穿过三个山塘到隔壁的苏州村。听到这声音,乡亲们会拿出一个大碗或一个水瓢,端两块尚热乎乎、颤巍巍、水灵灵的豆腐。端了豆腐的人家路上遇到熟人时总要略带自嘲道“没嘛概菜食(客家方言没什么菜吃的意思),煎两块豆腐炒辣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一元钱两块的豆腐也算餐桌上的“罕见”品,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舍得慷慨“解馋”的,农村人平时饮食节俭,总能就着菜园里现成的菜和坛子里的菜干对付着一日三餐。某日如果被母亲吩咐端几块豆腐,我一定早早站在家门口候着卖豆腐的耀云叔,瞪着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吆喝声由远至近,生怕错过。端到手的豆腐,洁白嫩滑,豆香扑鼻而来,稳稳当当地把豆腐放在灶台时,我似乎已经品尝到了似的,有一种简单的快乐与满足。
那个年代,田土是没有一刻闲着,没有一寸荒着的,家家户户都要在稻田埂上、果树下的空地、暂未成器的菜地旁、羊肠小道、犄角旮旯里种上豆子。当晚稻还未掀起金色波浪,大豆就先给稻田镶上了金边,收获的黄豆总能带给乡村的孩子诸多惊喜。
做豆腐、煎豆腐,是过年的必备,通常也只在农闲冬至前后才做,当整个村子弥漫豆腐香,我们就知道年不远了。做豆腐是一门技术活,程序复杂,还大有学问。经验丰富、技术老到的人,一斤黄豆能出三斤半豆腐,技术差、火候掌握不好的,可能一斤半都出不来,而且豆腐还老,不鲜嫩。母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农活好手,常被请去当蒸酒、磨豆腐的“教导员”。
“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一年一次的做豆腐总是特别隆重,如果年豆腐做得特别好,母亲会异常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好兆头,明年运气不会差。如果不太理想,母亲也会来电话提醒出门在外,为人处世要小心谨慎。于是做豆腐从浸黄豆、磨豆子、煮豆浆、兑石膏水,一步也不敢马虎。洗好的豆子通常要浸泡一天一夜,等充分喝饱水后,用石磨磨出奶白奶白的豆汁,加山泉水倒入大铁锅煮,煮得沸腾后,将豆汁倒入白色的布袋,用力挤压滤渣,留下细腻的豆浆。之后便是最关键的一步——点浆,所谓点浆,即将事前在灶里烧熟的石膏按一定比例研磨成石膏水,给豆浆加入凝固剂。剂量不能多也不能少,融合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温度要掐算得刚刚好,石膏水倒入豆浆盆中迅速搅匀,盖上锅盖,焖几分钟,豆浆就变成豆腐了。母亲掌握点豆腐的火候,除了经验,还会用一根筷子垂直地落下检验,当筷子能稳稳立住时,就可以上箱了。把水豆腐舀到用洁白的纱布铺好的方正豆腐格板箱里包裹起来,静静放置几个小时,等多余的水分沥干,水豆腐就大功告成了。母亲做的水豆腐特别厚实、嫩滑,做出来的霉豆腐更是全村一绝。
在炎陵人的口中,豆腐谐音“都福”“都富”,寓意着大家都福禄安康、都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户早已不再吝啬口袋的几块钱,已经实现了小康的梦想,也很少再有人自磨豆腐了。虽然年迈的母亲每年总要叨叨今年不做豆腐了,跑回老家的油钱都够买一年的豆腐了,还难收拾物件,可每到冬至总还是忍不住重新操起大铁锅、豆腐磨坊、豆腐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