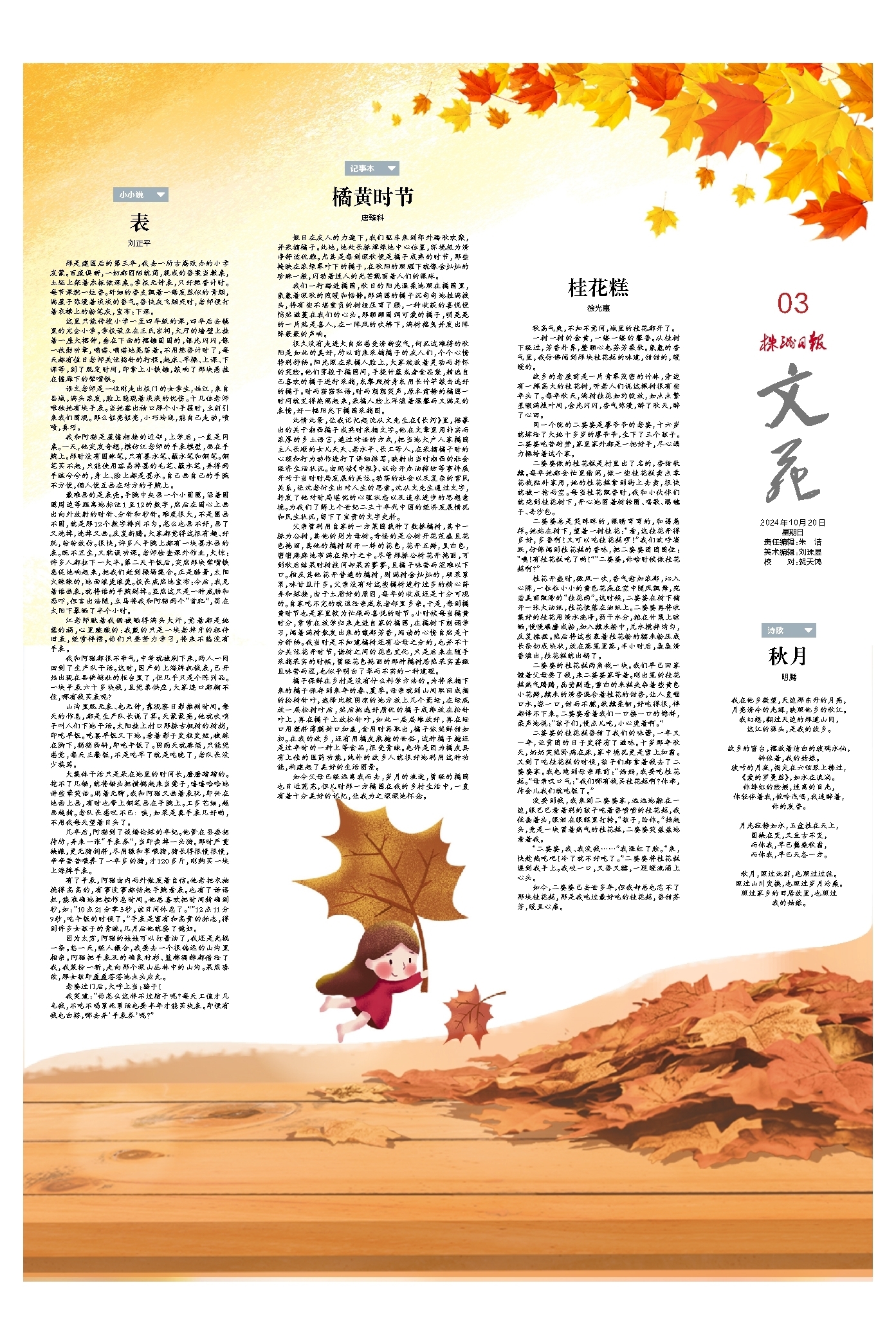表
刘正平
那是建国后的第三年,我去一所古庵改办的小学发蒙。百废俱新,一切都因陋就简,现成的香案当教桌,土坯上架着木板做课桌。学校无钟表,只好燃香计时。每节课燃一炷香。纤细的香支飘着一绺发丝似的青烟,满屋子弥漫着淡淡的香气。香快灰飞烟灭时,老师便打着衣襟上的粉笔灰,宣布:下课。
这里只能传授小学一至四年级的课,四年后去镇里的完全小学。学校设立在王氏宗祠,大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座大摆钟,垂在下面的摆锤圆圆的,银光闪闪,像一枚勋功章,嘀嗒、嘀嗒地晃荡着。不用燃香计时了,每天都有值日老师关注指针的行程。起床、早操、上课、下课等,到了既定时间,即拿上小铁锤,敲响了那块悬挂在檐廊下的犂嘴铁。
语文老师是一位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姓江,来自县城,满头浓发,脸上隐现着淡淡的忧伤。十几位老师唯独她有块手表。当她露出袖口那个小手箍时,立刻引来我们围观。那么锃亮锃亮,小巧玲珑,能自己走动,啧啧,真巧。
我和阿猫是屋檐相接的近邻,上学后,一直是同桌。一天,他突发奇想,模仿江老师的手表模型,画在手腕上。那时没有圆珠笔,只有墨水笔、蘸水笔和钢笔。钢笔买不起,只能使用容易掉墨的毛笔、蘸水笔,弄得两手脏兮兮的,身上、脸上都是墨水。自己画自己的手腕不方便,俩人便互画在对方的手腕上。
最难画的是表壳。手腕中央画一个小圆圈,沿着圆圈周边等距离地标注1至12的数字,然后在圆心上画出向外放射的时针、分针和秒针。难度很大,不是圈画不圆,就是那12个数字排列不匀。怎么也画不好,画了又洗掉,洗掉又画。反复折腾。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好玩,纷纷效仿。很快,许多人手腕上都有一块墨水画的表。既不卫生,又耽误功课。老师检查课外作业,大惊:许多人都拉下一大半。第二天午饭后,突然那块犂嘴铁急促地响起来,把我们赶到操场集合。正是酷暑,太阳火辣辣的,地面滚烫滚烫。校长威然地宣布:今后,我见着谁画表,就将谁的手腕剁掉。显然这只是一种威胁和恐吓,但言出法随,立马将我和阿猫两个“首犯”,罚在太阳下暴晒了半个小时。
江老师瞅着我俩被晒得满头大汗,觉着都是她惹的祸,心里酸酸的:我戴的只是一块老掉牙的祖传旧表,经常停摆。你们只要努力学习,将来不愁没有手表。
我和阿猫都很不争气,中考就被刷下来,两人一同回到了生产队干活。这时,国产的上海牌机械表,已开始出现在县供销社的柜台里了,但几乎只是个陈列品。一块手表六十多块钱,且凭票供应,大家连口都糊不住,哪有钱买表呢?
山沟里既无表、也无钟,靠观察日影推测时间。每天的作息,都是生产队长说了算。天蒙蒙亮,他就吹哨子叫人们下地干活。太阳挂上村口那株古枫树的树梢,即吃早饭。吃罢早饭又下地。看着影子变粗变短,被踩在脚下,稍稍西斜,即吃午饭了。阴雨天就麻烦,只能凭感觉,每天三餐饭,不是吃早了就是吃晚了,老队长没少挨骂。
大集体干活只是呆在地里的时间长,磨磨蹭蹭的。挖不了几锄,就将锄头把横搁起来当凳子,嘻嘻哈哈地讲些荤笑话。闲着无聊,我和阿猫又画着表玩,即兴在地面上画,有时也带上钢笔画在手腕上。工多艺细,越画越精。老队长感叹不已: 唉,如果是真手表几好哟,不用我每天望着日头了。
几年后,阿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爹在县委招待所,弄来一张“手表券”,当即卖掉一头猪。那时严重缺粮,更无猪饲料,尽用糠和草喂猪,猪长得很慢很慢,辛辛苦苦喂养了一年多的猪,才120多斤,刚夠买一块上海牌手表。
有了手表,阿猫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他老把衣袖挽得高高的,有事没事都抬起手腕看表。也有了话语权,能准确地把控作息时间。他总喜欢把时间精确到秒,如:“10点21分零3秒,该日间休息了。”“12点11分9秒,吃午饭的时候了。”手表是富有和高贵的标志,得到许多女孩子的青睐。几月后他就娶了媳妇。
因为太穷,阿猫的娃娃可以打酱油了,我还是光棍一条。忽一天,经人撮合,我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山沟里相亲。阿猫把手表及的确良衬衫、蓝棉绸裤都借给了我,我装扮一新,走向那个深山丛林中的山沟。果然凑效,那女孩即羞羞答答地点头应允。
老婆过门后,大呼上当:骗子!
我笑道:“你怎么这样不过脑子呢?每天工值才几毛钱,不吃不喝累死累活也要半年才能买块表。即便有钱也白搭,哪去弄‘手表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