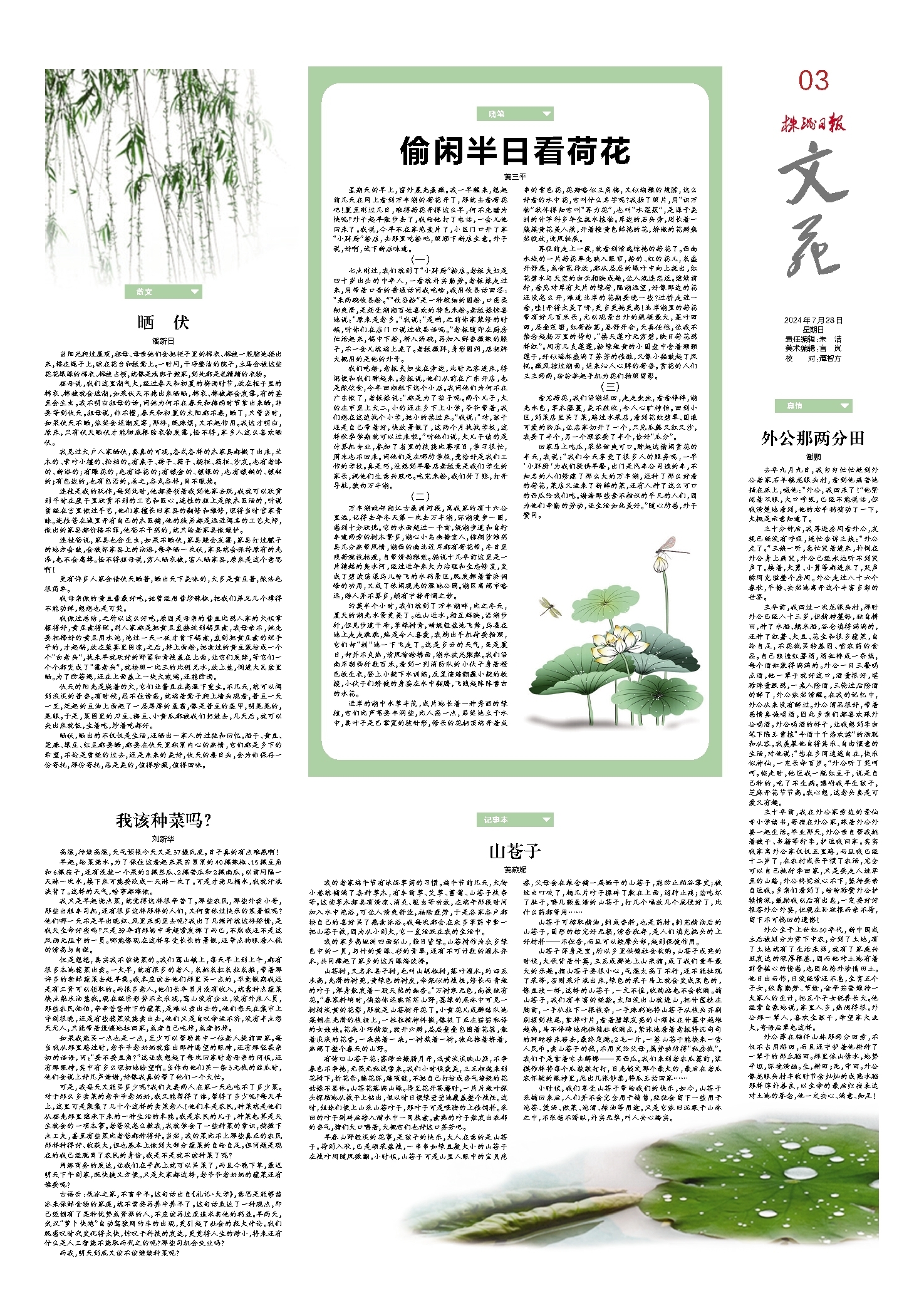外公那两分田
谢鹏
去年九月九日,我匆匆忙忙赶到外公老家石羊镇龙眼头村,看到他痛苦地躺在床上,喊他:“外公,我回来了!”他紧闭着双眼,大口呼吸,已经不能说话,但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右手稍稍动了一下,大概是示意知道了。
三十分钟后,我再进房间看外公,发现已经没有呼吸,连忙告诉三姨:“外公走了。”三姨一听,急忙哭着进来,扑倒在外公身上痛哭,外公已经永远听不到哭声了。接着,大舅、小舅等都进来了,哭声瞬间充溢整个房间。外公走过八十六个春秋,平静、安然地离开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三年前,我回过一次龙眼头村,那时外公已经八十三岁,但精神矍铄,独自耕田,种了水稻、糯米稻,谷仓填得满满的,还种了红薯、大豆、花生和很多蔬菜,自给自足,不花钱买转基因、喷农药的食品。自己酿造红薯酒,酒缸排成一条线,每个酒缸装得满满的。外公一日三餐喝点酒,他一辈子就好这口,酒量很好,堪称海量级别,一桌人陪酒,三轮过后陪酒的醉了,外公依然清醒。在我的记忆中,外公从来没有醉过。外公酒品很好,带着感情真诚喝酒,因此乡亲们都喜欢跟外公喝酒。外公喝酒的样子,让我想到李白笔下陈王曹植“斗酒十千恣欢谑”的洒脱和从容。我羡慕他自得其乐、自由惬意的生活,对他说:“您在乡间逍遥自在,快乐似神仙,一定长命百岁。”外公听了笑呵呵。临走时,他送我一瓶红豆子,说是自己种的,吃了不生病。嘱咐我早生孩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心想,这老头真是可爱又有趣。
三十年前,我在外公家旁边的景仙寺小学读书,寄宿在外公家,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毕业那天,外公亲自帮我挑着被子、书籍等行李,护送我回家。其实我家离外公家仅仅五里路,而且我已经十二岁了,在农村成长干惯了农活,完全可以自己挑行李回家,只是要走人迹罕至的山路,外公终究放心不下,坚持要亲自送我。乡亲们看到了,纷纷称赞外公护犊情深,鼓励我以后有出息,一定要好好报答外公外婆,但现在孙欲报而亲不待,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
外公生于上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被划分为贫下中农,分到了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生活来源,就有了家庭兴旺发达的深厚根基,因而他对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感,也因此格外珍惜田土。他日出而作,日没经常还不息,生育五个子女,依靠勤劳、节俭,含辛茹苦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把五个子女抚养长大。他经常自豪地说,家里人多,热闹得很。外公那一辈人,喜欢生孩子,希望家大业大,寄语后辈也这样。
外公葬在猫仔山林那两分田旁,不仅不占用稻田,而且还守护着他耕种了一辈子的那丘稻田。那里依山傍水,地势平坦,环境清幽。生,耕田;死,守田。外公像龙眼头村丰收时节金灿灿的成熟水稻那样淳朴善良,以生命的最后归宿表达对土地的眷念,他一定安心、满意、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