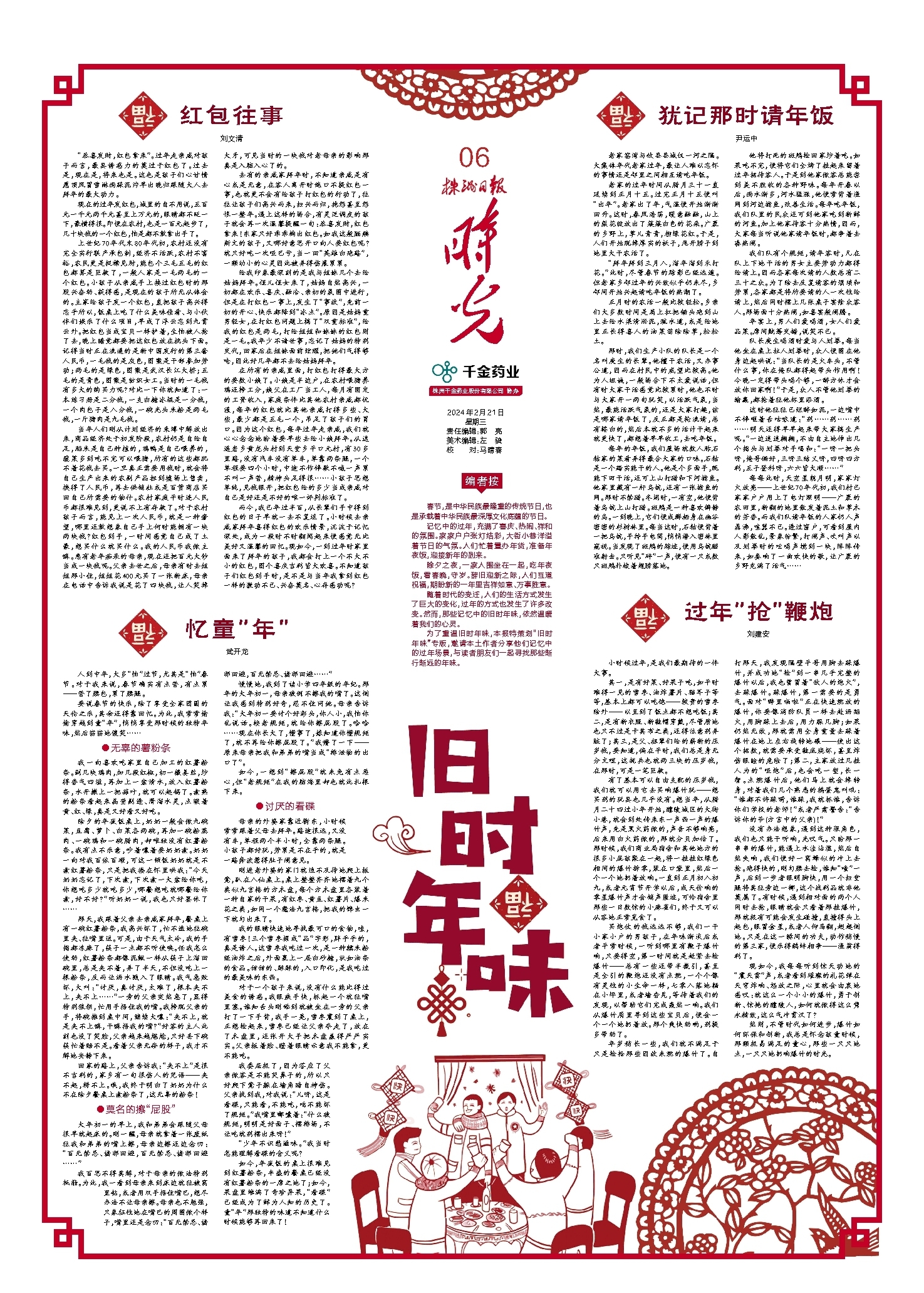犹记那时请年饭
尹运中
老家窑湾与攸县县城仅一河之隔。大集体年代老家过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还是邻里之间相互请吃年饭。
老家的过年时间从腊月三十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过完正月十五便叫“出年”。老家出了年,气温便开始渐渐回升。这时,春风浩荡,暖意融融,山上的梨花绽放出了簇簇白色的花朵。广袤的乡野上,草儿青青,柳绿花红。于是,人们开始脱掉厚实的袄子,甩开膀子到地里大干农活了。
“拜年拜到三月八,溜年溜到禾打花。”此时,尽管春节的踪影已经远遁。但老家乡邻过年的兴致似乎仍未尽,乡邻间开始兴起请吃年饭的热潮了。
正月时的农活一般比较轻松。乡亲们大多数时间是肩上扛把锄头跑到山上去给水渠清淤泥,疏水道,或是给地里正长得喜人的油菜苗除除草,松松土。
那时,我们生产小队的队长是一个名叫庚生的长辈。他擅干农活,又办事公道,因而在村民中的威望比较高。他为人坦诚,一般场合下不太爱说话,但有时大家干活感觉比较累时,他也不时与大家开一两句玩笑,以活跃气氛,当然,最能活跃气氛的,还是大家打趣,该是哪家请年饭了,反正都是轮流请,总有搭白的,然后本就不多的活计干起来就更快了,都想着早早收工,去吃年饭。
每年的年饭,我们屋场就数人称石牯家的菜肴弄得最合大家的口味。石牯是一个踏实能干的人。他是个多面手,既能下田干活,还可上山打猎和下河捕鱼。他家里藏有一杆鸟铳,还有一张捕鱼的网。那时不禁猎。冬闲时,一有空,他便背着鸟铳上山打猎。斑鸠是一种喜欢僻静的鸟。一到晚上,它们便成群栖身在幽谷密密的杉树林里。每当这时,石牯便背着一把鸟铳,手持手电筒,悄悄潜入密林里窥视。当发现了斑鸠的踪迹,便用鸟铳瞄准射击。只听见“砰”一声,便有一只或数只斑鸠扑棱着翅膀落地。
他将打死的斑鸠捡回家炒着吃。如果吃不完,便将它们全烤了挂起来留着过年招待客人。于是到他家做客总能尝到美不胜收的各种野味。每年开春以后,雨水渐多,河水猛涨,他便常背着渔网到河边捕鱼,改善生活。每年吃年饭,我们队里的民众还可到他家吃到新鲜的河鱼。加上他家待客十分热情,因而,大家每当听说他家请年饭时,都争着去凑热闹。
我们队有个规矩,请年客时,凡在队上下地干活的男女主要劳动力都得给请上。因而各家每次请的人数总有二三十之众。为了除去反复请客的烦琐和劳累,各家都是将所要请的人一次性给请上,然后同时摆上几张桌子宴飨众客人。那场面十分热闹,如喜宴般闹腾。
年宴上,男人们爱喝酒,女人们爱品菜。席间觥筹交错,说笑不已。
队长庚生喝酒时爱与人划拳。每当他坐在桌上拉人划拳时,众人便围在他身边起哄说:“当队长的是火车头,不管什么事,你在俺队都得起带头作用啊!今晚一定得带头喝个够,一醉方休才会放你回家啊!”于是,众人不管他划拳的输赢,都抢着往他杯里添酒。
这时他往往已烂醉如泥,一边嘴中不停咂着舌咕哝道:“别……别……别……明天还得早早起来带大家搞生产呢。”一边迷迷糊糊,不由自主地伸出几个指头与划拳对手唱和:“一呀一把头呀,俺哥俩好,三呀三结义呀,四呀四方利,五子登科呀,六六皆大顺……”
每每此时,天空星朗月明,家家灯火放亮——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村已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照明——广袤的农田里,新翻的地里散发着泥土和草木的芳香。而我们队请年饭的人家仍人声鼎沸,喧嚣不已。透过窗户,可看到屋内人影散乱,景象纷繁,打闹声、吹叫声以及划拳时的吆喝声搅到一块,阵阵传来,如奏响了一曲欢快的歌,让广袤的乡野充满了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