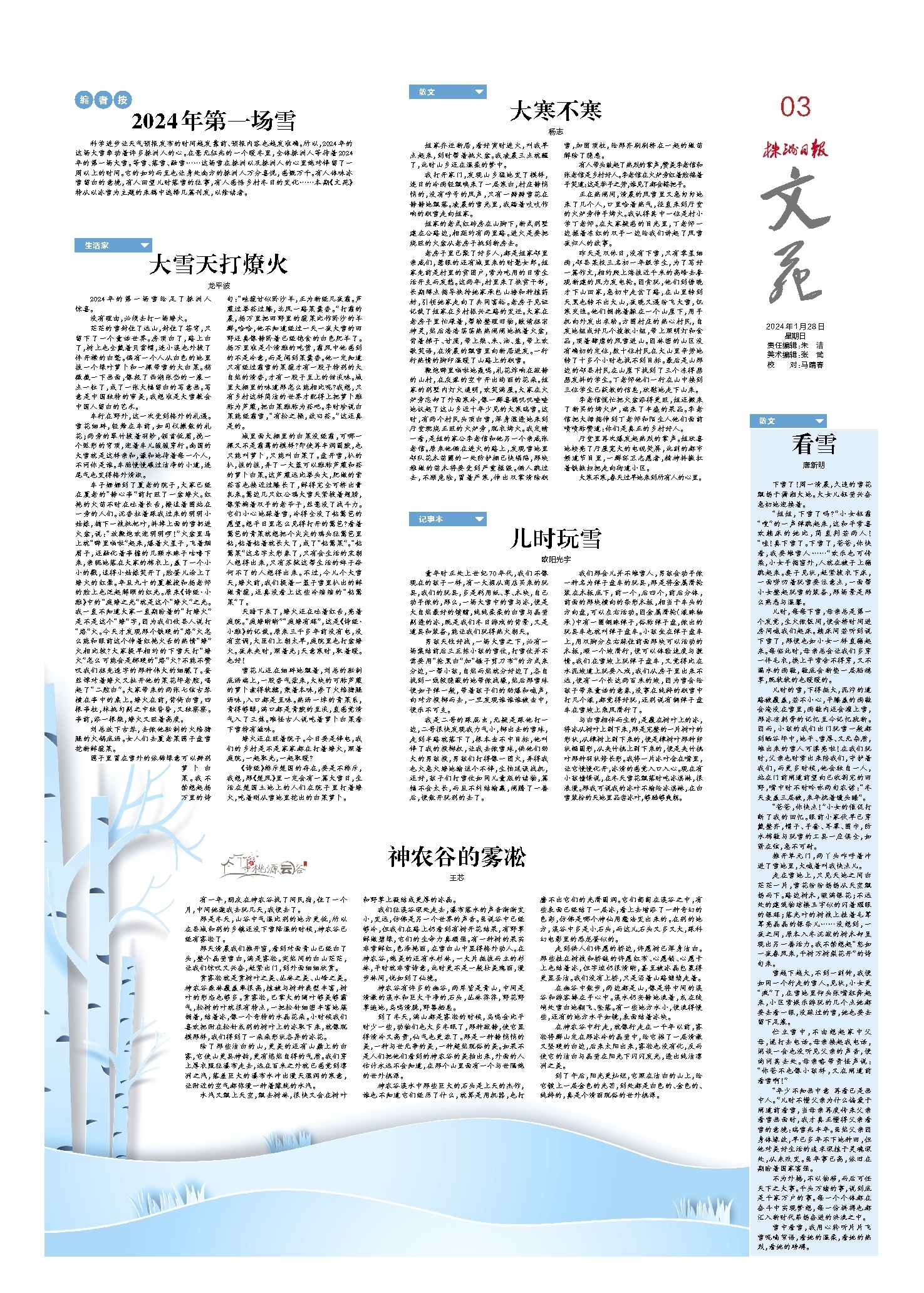大雪天打燎火
龙平波
2024年的第一场雪给足了株洲人惊喜。
没有理由,必须去打一场燎火。
茫茫的雪封住了远山,封住了苍穹,只留下了一个童话世界。房顶白了,路上白了,树上也全戴着贝雷帽,连小溪也外披了件开襟的白氅。偶有一个人从白色的地里拔一个绿叶萝卜和一棵带雪的大白菜。稍微截一下画面,像极了西湖张岱的一痕一点一粒了,成了一张大幅留白的写意画。写意是中国独特的审美,我想准是大雪教会中国人留白的艺术。
车行在野外,这一次受到格外的礼遇。雪花细碎,轻舞在车前,如司仪撒散的礼花;两旁的翠竹披着羽纱,颔首低眉,挽一个弧形的穹顶,迎着车儿缓缓穿行。南国的大雪就是这样亲和,谦和地待着每一个人,不问你是谁。车胎慢慢碾过洁净的小道,连尾气也变得格外清淑。
车子姗姗到了夏老的院子,大家已经在夏老的“静心亭”前打旺了一盆燎火。红艳的火苗不时在吐着长舌,撩逗着围站在一旁的人们。沉香拉着跟我过来的玥玥小姑娘,摘下一枝枇杷叶,抖掉上面的雪扔进火盆,说:“放鞭炮欢迎玥玥啰!”火盆里马上就“噼里啪啦”起来,爆着火星子,飞着烟眉子,还融化着亭檐的几颗水珠子咕噜下来,亲昵地落在大家的棉衣上,盖了一个小小的戳,逗得小姑娘笑开了,脸蛋儿涂上了燎火的红晕。年且九十的夏教授和杨老师的脸上也泛起解颐的红光。原来《诗经·小雅》中的“庭燎之光”就是这个“燎火”之光。我一直不知道大家一直期盼着的“打燎火”是不是这个“燎”字,因为我们攸县人说打“烙”火。今天才发现那个铁硬的“烙”火怎么能和眼前这个伸着红艳火舌的热情“燎”火相比较?大家提早相约的下雪天打“燎火”怎么可能会是梆硬的“烙”火?不能不赞叹我们祖先造字的那种伟大的细腻了。蚕丝谭对着燎火又扯开他的菜花坪老腔,唱起了“二腔白”。大家带来的两张七弦古琴横在亭中的桌上。燎火在前,背倚白雪,四根亭柱,抹挑勾剔之中独昏昏,又独察察。亭前,添一根柴,燎火又旺着高度。
刘总放下古琴,去做他秘制的火焙猪腿的火锅底汤。女人们去夏老菜园子盘雪挖新鲜蔬菜。
园子里冒在雪外的依稀绿意可以辨别萝卜白菜。我不禁想起杨万里的诗句:“畦蔬甘似卧沙羊,正为新经几夜霜。芦菔过拳菘过膝,北风一路菜羹香。”打霜的晨,杨万里把田野里的蔬菜比作卧沙的羊群。哈哈,他不知道经过一天一夜大雪的田野还真像静卧着已经饱食的白色肥羊了。杨万里准是个清雅的吃货,霜风中他感到的不是冷意,而是闻到菜羹香。他一定知道只有经过霜雪的菜蔬才有一股子特别的大自然的清香,才有一股子至上的甜淡味。城里大棚里的味道那怎么能相比呢?我想,只有乡村这样简洁的世界才配得上把萝卜雅称为芦菔,把白菜雅称为菘吧。李时珍说白菜能经霜雪,“有松之操,故曰菘。”这还真是的。
城里面大棚里的白菜没经霜,可哪一棵又不是霜蔫的模样?即使再丰润圆腴,也只能叫萝卜,只能叫白菜了。盘开雪,扒的扒,拔的拔,弄了一大篮可以雅称芦菔和菘的萝卜白菜。这芦菔远比拳头大,肥嫩的紫菘苔也接近过膝长了,鲜得完全可挤出膏乳来。篱边几只红公鸡大雪天紧掖着翅膀,像紧掏着双手的老爷子,丝毫没了战斗力。它们小心地踩着雪,冷得全没了钻篱笆的愿望。想平日里怎么见得打开的篱笆?看着篱笆的青菜就想把个尖尖的鸡头往篱笆里钻,钻着钻着就长大了,成了“钻篱菜”。“钻篱菜”这名字太形象了,只有会生活的宋朝人想得出来,只有苏轼这帮生活的绊子奈何不了的人想得出来。不过,今儿个大雪天,燎火前,我们提着一篮子雪里扒出的鲜嫩青蔬,还真没看上这些冷缩缩的“钻篱菜”了。
天暗下来了,燎火还在吐着红舌,亮着庭院。“庭燎晰晰”“庭燎有辉”,这是《诗经·小雅》的记载。原来三千多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大臣们上朝太早,庭院里也打盆燎火。夜未央时,照着光;天意寒时,取着暖。也好!
雪花儿还在细碎地飘着,刘总的秘制底汤端上,一股香气袭来,大块的可称芦菔的萝卜煮得软糯,秉着本味,渗了火焙猪腿汤味,入口都是至味。热汤一焯的青菜系,青得够醇,满口都是青腴的至淡,直感觉清气入了三焦。难怪古人说吃着萝卜白菜看下雪特有滋味。
燎火还在旺着院子。今日要是停电,我们的乡村是不是家家都在打着燎火,照着庭院,一起取光,一起取暖?
《诗经》排斥楚国的存在,要是不排斥,我想,那《楚风》里一定会有一篇大雪日,生活在楚国土地上的人们在院子里打着燎火,吃着刚从雪地里挖出的白菜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