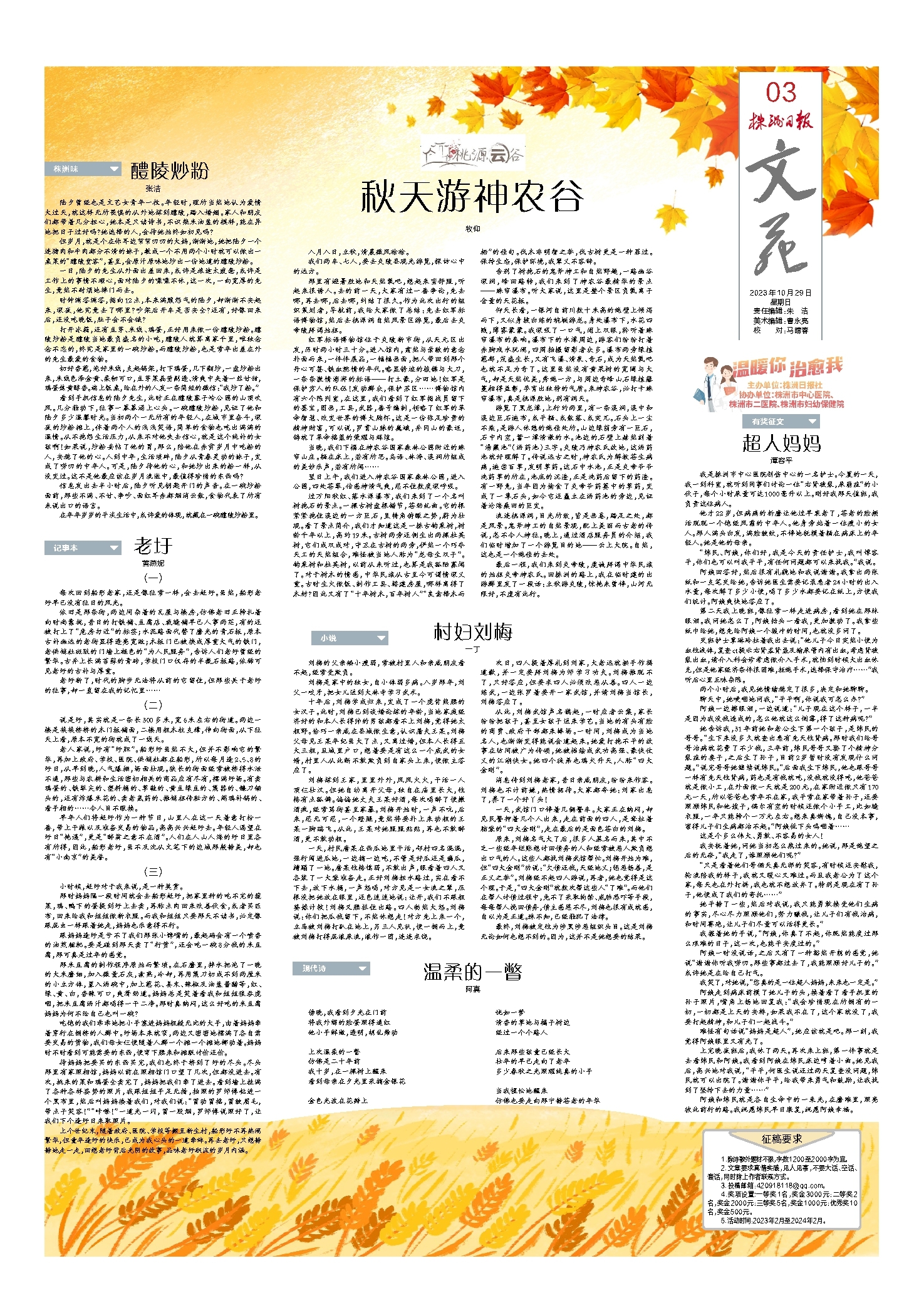老圩
黄燕妮
(一)
每次回到船形老家,还是像往常一样,会去赶圩。虽然,船形老圩早已没有往日的风光。
依旧是那条街,两边间杂着的瓦屋与楼房,仿佛老旧正挣扎着向时尚靠拢,昔日的打铁铺、豆腐店、裁缝铺早已人事两茫,有的还被打上了“危房勿近”的标签;水泥路面代替了磨光的青石板,原本古朴幽远的老街显得透亮宽敞;木板门已被换成厚重大气的铁门,老供销社斑驳的门墙上褪色的“为人民服务”,告诉人们老圩曾经的繁华。古井上长满苔藓的青砖,学校门口仅存的半截石板路,依稀可见老圩的古朴与厚重。
老圩新了,时代的脚步无法将从前的它留住,但那些关于老圩的往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
说是圩,其实就是一条长300多米,宽6米左右的街道。两边一楼是挨挨挤挤的木门板铺面,二楼用粗木柱支撑,伸向街面,从下往天上看,原本不宽的街就成了一线天。
老人家说,圩有“圩胆”。船形圩虽然不大,但并不影响它的繁华,再加上政府、学校、医院、供销社都在船形,所以每月逢2、5、8的圩日,从早到晚,人气爆棚,场面壮观。狭长的街面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那些与农耕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应有尽有,摆满圩场。有卖鸡蛋的、铁犁尖的、塑料桶的、草鞋的、黄豆绿豆的、篾器的、镰刀锄头的,还有炸爆米花的、卖老鼠药的、推销祖传秘方的、阉鸡补锅的、看手相的……令人目不暇接。
早年人们将赶圩作为一种节日,山里人在这一天着意打扮一番,带上干粮以及准备交易的物品,高高兴兴赶圩去。年轻人渴望在圩日“艳遇”,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们在人山人海的圩日里各有所得,因此,船形老圩,虽不及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那般静美,却也有“小南京”的美誉。
(三)
小时候,赶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奖赏。
那时妈妈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船形赶圩,把家里种的吃不完的蔬菜,鸡、鸭下的蛋提到圩上去卖,再称点肉回来改善伙食,或者买匹布,回来给我和姐姐做新衣服。而我和姐姐只要那天不读书,必定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她走,妈妈也乐意得不行。
跟妈妈逢圩是亏不了我们那张小馋嘴的,最起码会有一个喷香的油煎糍粑。要是碰到那天卖了“行货”,还会吃一碗8分钱的米豆腐,那可真是过年的感觉。
那米豆腐的制作程序原始而繁琐。在石磨里,拌水把泡了一晚的大米磨细,加入微量石灰,煮熟,冷却,再用篾刀切成不到两厘米的小立方体,置入汤碗中,加上葱花、姜末、辣椒及油盐酱醋等,红、绿、黄、白,香辣可口,爽滑劲道。妈妈总是笑着看我和姐姐狼吞虎咽,把米豆腐汤汁都喝得一干二净。那时真纳闷,这么好吃的米豆腐妈妈为何不给自己也叫一碗?
吃饱的我们乖乖地把小手塞进妈妈粗糙无比的大手,由着妈妈牵着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圩场本来就窄,两边又密密地摆满了各自需要交易的货物,我们母女仨便随着人群一个摊一个摊地挪动着。妈妈时不时看到可能需要的东西,便弯下腰来和摊贩讨价还价。
待妈妈把要买的东西买完,我们也终于挤到了圩的尽头。尽头那里有家照相馆,妈妈以前在照相馆门口望了几次,但都没进去。有次,挑来的菜和鸡蛋全卖完了,妈妈把我们牵了进去。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姿势的照片,我跟姐姐手足无措,拍照的罗师傅钻进一个黑布里,然后叫妈妈搂着我们,对我们说:“冒动冒摇,冒皱眉毛,带点子笑容!”“咔嚓!”一道光一闪,冒一股烟,罗师傅说照好了,让我们下个逢圩日来取照片。
上个世纪末,随着政府、医院、学校等搬至新生村,船形圩不再热闹繁华,但童年逢圩的快乐,已成为我心头的一道牵绊。再去老圩,只想静静地走一走,回想老圩背后光阴的故事,品味老圩积淀的岁月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