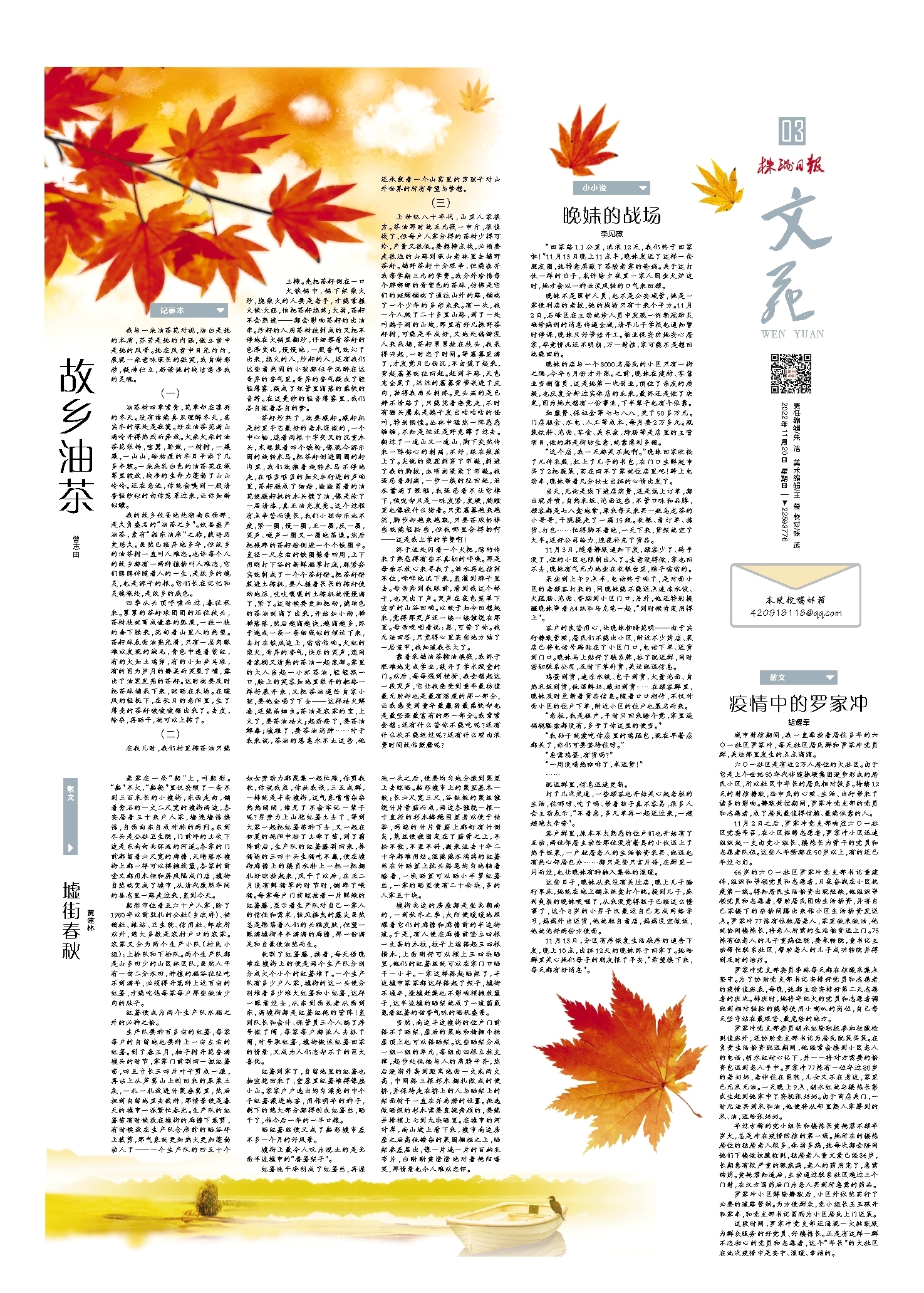墟街春秋
散文
黄建林
老家在一条“船”上,叫船形。“船”不大,“船舱”里仅安顿了一条不到三百米长的小墟街,东西走向,铺着青石的一丈二尺宽的墟街两边,各安居着三十来户人家,墙连墙栋接栋,自西向东自成对称的两列。东到尽头是公社卫生院,门前坪的土坎下边是东南向北环流的河道。各家的门前都留着六尺宽的廊檐,天晴落水墟街上都一样可以摆摊放篮,各家的前堂又都用木柜和屏风隔成门店,墟街自然就变成了墟市,从清代康熙年间的县志里一路走过来,直到今天。
船形市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除了1980年以前驻扎的公社(乡政府)、供销社、粮站、卫生院、信用社、邮政所以外,绝大多数是农村户口的农家。农家又分为两个生产小队(村民小组):上桥队和下桥队。两个生产队都是山多田少的山区林区队,虽然人平有一亩二分水田,种植的稻谷往往吃不到满年,必须得开荒种上近百亩的红薯,才能吃饱每家每户那些缺油少肉的肚子。
红薯便成为两个生产队水稻之外的必种之物。
生产队要种百多亩的红薯,每家每户的自留地也要种上一亩左右的红薯。到了春三月,柚子树开花香满墟头的时节,家家门前割回一担红薯苗,四五寸长三四片叶子剪成一截,再沾上从芦箕山上刨回来的尿浆土灰,一扎一扎放进竹篾畚箕里,然后担到自留地里去栽种,那情景便是春天的墟市一派繁忙春光。生产队的红薯苗有时候放在墟街的廊檐下裁剪,有时候放在生产队仓库前的晒谷坪上裁剪,那气象就更加热火更加蓬勃动人了——一个生产队的四五十个妇女劳动力都聚集一起忙碌,你剪我收,你说我应,你扯我谈,三五成群,一排就是半条墟街,这气象嘈嘈杂杂热热闹闹,谁见了不会牢记一辈子呢?男劳力上山挖红薯土去了,等到大家一起把红薯苗种下去,又一起在初夏的艳阳中松了土牵了苗,到了霜降前后,生产队的红薯藤割回来,养猪场的三四十头生猪吃不赢,便在墟街廊檐上的楼负水料上一把一把捆扎好晾挂起来,风干了以后,在正二月没有鲜猪草的时节时,铡碎了喂猪。每家每户门前晾挂着一片鲜绿的红薯藤,显示着生产队对自己一家人的信任和需求,轻风摇曳的藤尖虽然总是拂荡着人们的头脑发肤,但望一眼满墟街丰丰满满的廊檐,那一份满足和自豪便油然而生。
收割了红薯藤,接着,每天傍晚堆在墟街上的便是两个生产队分别分成大个小个的红薯堆了。一个生产队有多少户人家,墟街的这一头便分别堆着多少堆大红薯和小红薯,这样一眼看过去,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满墟街都是红薯红艳的营阵!直到队长和会计、保管员三个人编了序号做了阄,每家每户都派人去抓了阄,对号取红薯,墟街搬运红薯回家的情景,又成为人们忘却不了的巨大喜悦。
红薯到家了,自留地里的红薯也抽空挖回来了,堂屋里红薯堆得像座小山。家家户户选出均匀漂亮的中个子红薯藏进地窖,用作明年的种子,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得刨成红薯丝,晒干了,作今后一年的一半口粮。
晒红薯丝便又成了船形墟市差不多一个月的好风景。
墟街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北面半边墟市的“番薯架子”。
红薯洗干净刨成了红薯丝,再漂洗一次之后,便要均匀地分撒到篾笪上去晾晒。船形墟市上的篾笪基本一致:长六尺宽三尺,谷粒粗的篾丝缠绕竹片骨筋而成,两边各缠绕一根一寸直径的杉木棒稳固笪身以便于抬举,两端的竹片骨筋上都钉有竹倒尖,篾丝便被固定在了筋骨之上,不松不散,不歪不斜,搬来运去十年二十年都难用烂。湿漉漉水漓漓的红薯丝在竹晒笪上枕头搭尾均匀地躺着睡着,一块晒笪可以晒小半箩红薯丝,一家的晒笪便有二十余块,多的人家五十块。
墟街北边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一到秋冬之季,太阳便暖暖地照耀着它们的廊檐和廊檐前的半边街道。于是,有人便在廊檐前竖立四根一丈高的木柱,柱子上端搭起三四根横木,上面刚好可以摆上三四块晒笪,他们的红薯丝就可以在家门口晒干一小半。一家这样搭起晒架了,半边墟市家家都这样搭起了架子,墟街不通车,逢墟赶集也不影响摆摊放篮子,这半边墟的晒架就成了一道茵氤氲着红薯的甜香气味的晒秋盛景。
当然,南边半边墟街的住户门前搭不了晒架,屋后的菜地和猪棚牛栏屋顶上也可以搭晒架。这些晒架分成一组一组的单元,每组由四根立柱支撑,起步处低矮与人的肩膀平齐,然后逐渐升高到距离地面一丈或两丈高,中间搭三根杉木捆扎做成的便桥,并保持走在桥上的人与晒架上的架面树干一直在齐肩膀的位置。挑选做晒架的杉木需要直挺秀颀的,要能并排摆上七到九块晒笪。在墟市的河对岸,南山坡上看下来,墟市南边房屋之后高低错杂的菜园棚栏之上,晒架参差层出,像一片连一片的百衲衣布片,白晰晰黄澄澄地对着艳阳嘻笑,那情景也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