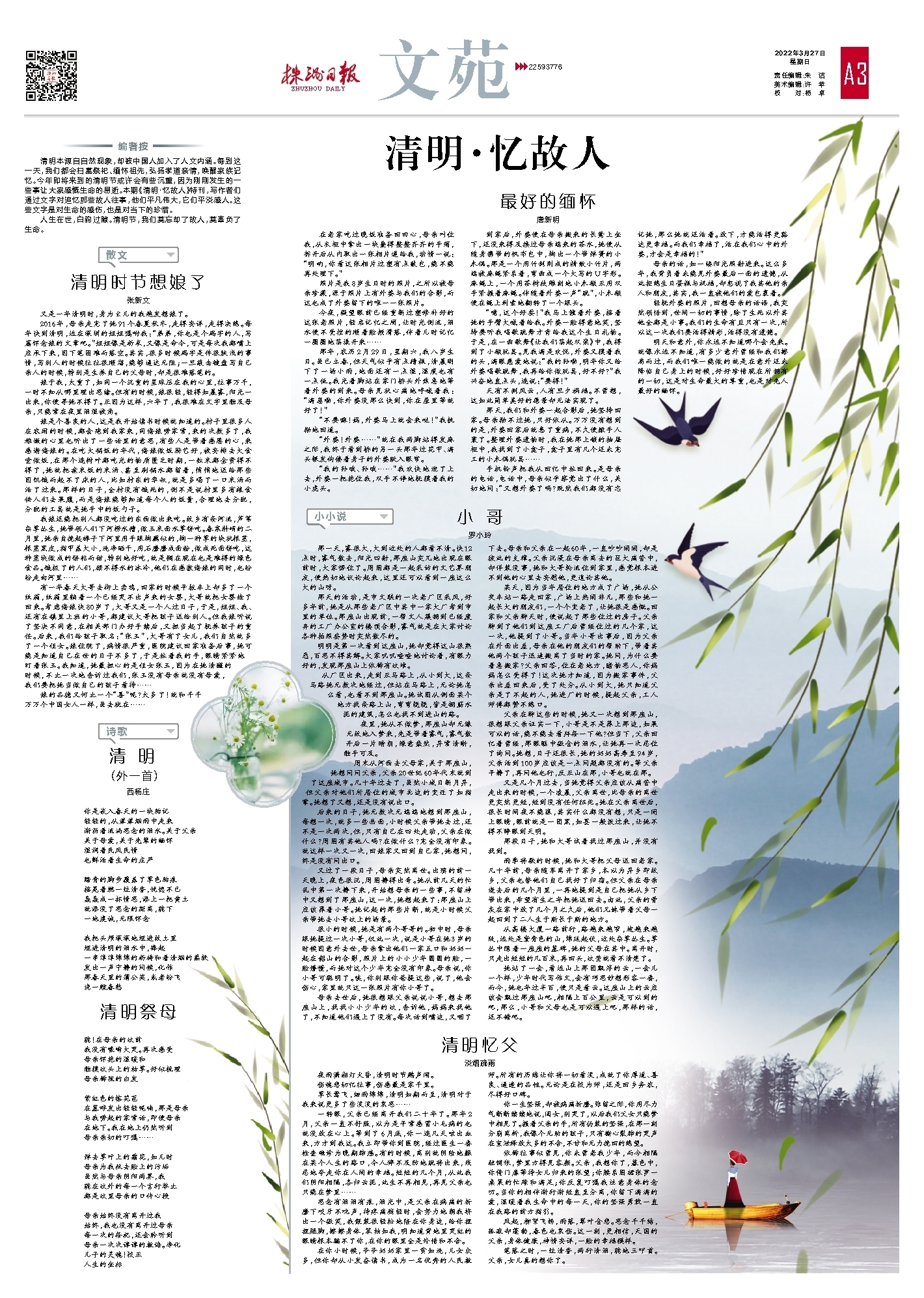清明时节想娘了
张新文
又是一年清明时,身为幺儿的我越发想娘了。
2016年,母亲走完了她91个春夏秋冬,走得安详,走得决绝。每年快到清明,远在深圳的姐姐嘱咐我:“弟弟,你也是个码字的人,写篇怀念娘的文章吧。”姐姐像是祈求,又像是命令,可是每次我都嘴上应承下来,因下笔困难而落空。其实,很多时候码字是件很肤浅的事情,写别人的时候往往很顺溜,能够通达无阻;一旦敲击键盘写自己亲人的时候,特别是生养自己的父母时,却是很难落笔的。
娘于我,太重了,如同一个沉重的星球压在我的心里,往事万千,一时不知从哪里理出思绪。但有的时候,娘很轻,轻得如晨雾,阳光一出来,你便寻她不得了。正因为这样,六年了,我很难在文字里触及母亲,只能常在夜里泪湿被角。
娘是个善良的人,这是我开始读书时候就知道的。村子里很多人在农闲的时候,都会跑到我家来,同俺娘唠家常,来的次数多了,我稚嫩的心里也听出了一些话里的意思,有些人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俺娘的。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俺娘做饭厨艺好,被安排去大食堂做饭,在那个连树叶都吃光的物质匮乏时期,一粒米都金贵得不得了,她就把煮米饭的米汤、甚至刷锅水都留着,悄悄地送给那些因饥饿而起不了床的人,比如村东的华叔,就是多喝了一口米汤而活了过来。那样的日子,全村没有饿死的,倒不是说村里多有粮食供人们去果腹,而是俺娘能够知道每个人的饭量,合理地去分配,分配的工具就是她手中的饭勺子。
我娘还能把别人都没吃过的东西做出来吃。故乡有条河流,芦苇杂草丛生,她带领人们下河捞水槽,做玉米面水草饼吃。春寒料峭的二月里,她亲自挽起裤子下河里用手跟掏藕似的,掏一种草的块状根茎,根茎黑皮,指甲盖大小,洗净晒干,用石磨磨成面粉,做成死面饼吃,这种茎块做成的饼粘而甜,特别地好吃,就是搁在现在也是难得的绿色食品。饿极了的人们,顾不得水的冰冷,他们在感激俺娘的同时,也纷纷走向河里……
有一年春天大哥去街上卖鸡,回家的时候平板车上却多了一个纸箱,纸箱里躺着一个已经哭不出声来的女婴,大哥就把女婴捡了回来。考虑俺娘快80岁了,大哥又是一个人过日子,于是,姐姐、我、还有在镇里上班的小哥,都建议大哥把孩子送给别人。但我娘听说了坚决不同意,在相关部门办好手续后,又担当起了抚养孩子的重任。后来,我们给孩子取名:“张玉”,大哥有了女儿,我们自然就多了一个侄女。娘住院了,病情很严重,医院建议回家准备后事,她可能是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于是拉着我的手,眼睛紧紧地盯着张玉。我知道,她最担心的是侄女张玉,因为在她清醒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们,张玉没有母亲就没有母爱,我们要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
娘的品德又何止一个“善”呢?太多了!就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女人一样,虽去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