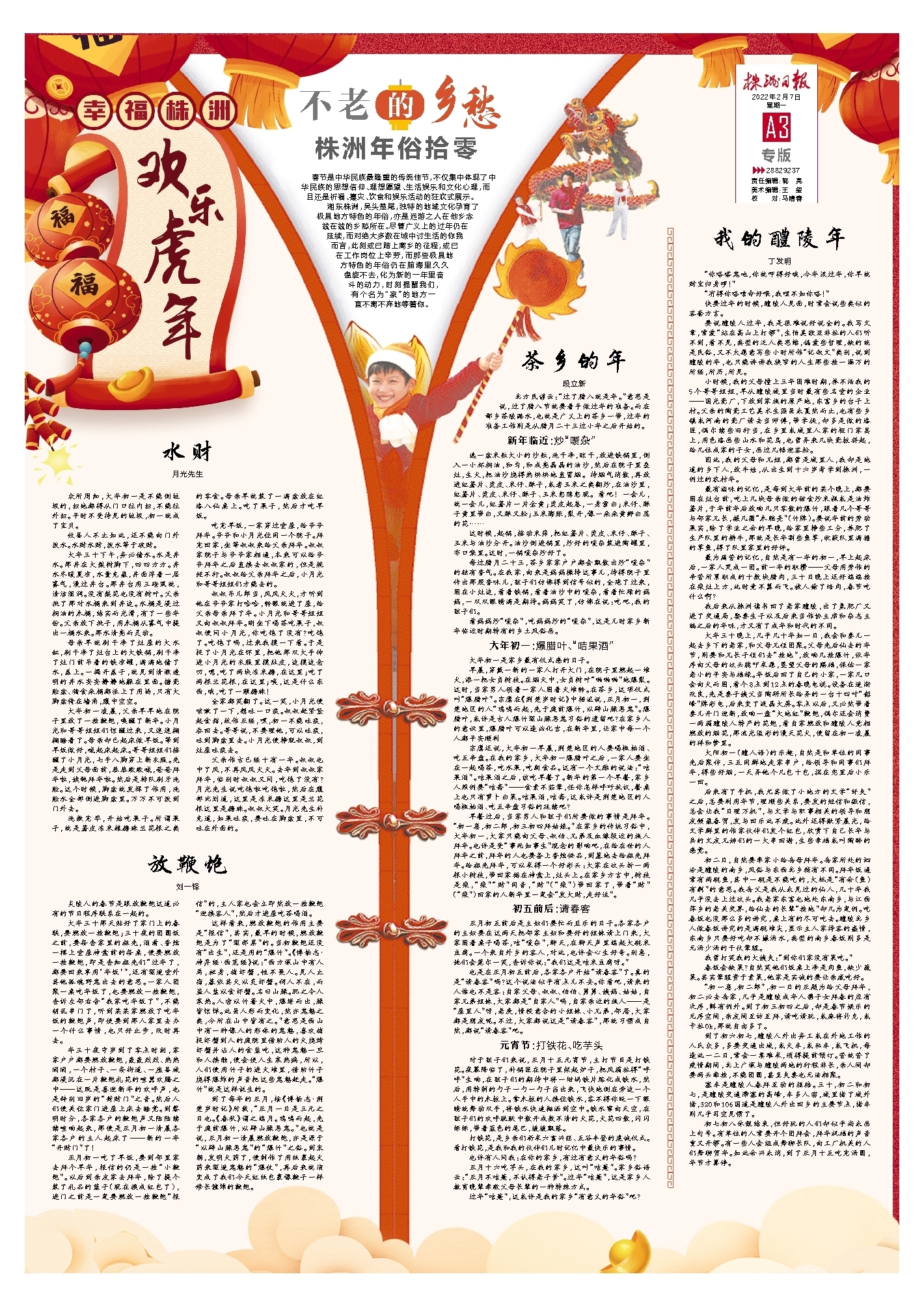我的醴陵年
丁发明
“你咯嗒鬼吔,你就呷得好哦,今年汲过年,你早就财宝归身啰!”
“冇得你咯嗦命好喂,我哩不如你咯!”
快要过年的时候,醴陵人见面,时常会说些类似的客套方言。
要说醴陵人过年,我是很难说好说全的。我写文章,常爱“站在高山上打锣”,生怕美欧亚非拉的人们听不到,看不见,典型的泛人类思维,偏爱些哲理,缺的就是民俗,又不太愿意写些小时所作“记叙文”类别,说到醴陵的年,也只能讲讲我狭窄的人生那些挂一漏万的所经,所历,所见。
小时候,我的父母撞上三年困难时期,养不活我的5个哥哥姐姐,早从醴陵城里当时最有些名堂的企业——国光瓷厂,下放到家族的原产地,东富乡的台子上村。父亲的陶瓷工艺美术生涯虽未戛然而止,也有些乡镇或河南的瓷厂请去当师傅,带学徒,却多是做的漆匠,偶尔续些旧行当,在乡里或城里人家的柜门家具上,用色漆画些山水和花鸟,也曾弄来几块瓷板拼起,给几位成家的子女,画过几幅迎客松。
因此,我的父母和兄姐,都曾是城里人,我却是地道的乡下人,放牛娃,从出生到十六岁考学到株洲,一例过的农村年。
最有滋味的记忆,是每到大年前的某个晚上,都要围在灶台前,吃上几块母亲做的甜食炒米糕或是油炸薯片,于年前年后放响几只零散的爆竹,跟着几个哥哥与邻家兄长,搓几圈“木脑壳”(竹牌)。要说年前的劳动果实,除了学业之余的早晚,给家里挣些工分,养肥了生产队里的耕牛,那就是长年割些鱼草,收获队里满塘的草鱼,得了队里家里的好评。
最为痛苦的记忆,自然是有一年的初一,早上起床后,一家人哭成一团。前一年的积攒——父母用劳作的辛苦所累积成的十数块腊肉,三十日晚上还好端端挂在柴灶上方,此时竟不翼而飞。被人偷了焙肉,春节吃什么啊?
我后来从株洲读书回了老家醴陵,出了氮肥厂又进了交通局,娶妻生子以及后来当作协主席和杂志主编之后的年味,才又有了成年和时代的不同。
大年三十晚上,几乎几十年如一日,我会和妻儿一起去乡下的老家,和父母兄侄团聚。父母先后仙去的年节,则要和兄长子侄们去“挂地”,放响几挂爆竹,依年序向父母的坟头跪叩求愿,垦望父母的赐福,保佑一家老小的平安与福禄。年饭后回了自己的小家,一家几口会向火而围,看个8点到12点的春晚电视。设备在逐渐改良,先是妻子姨父当陶研所长给弄的一台十四吋“韶峰”牌彩电,后来变了液晶大屏。零点以后,又必然带着妻儿开门迎新,放响一盘“大地红”鞭炮,偶尔还会消费一两箱醴陵人特产的花炮,看自家燃放和醴陵人竞相燃放的烟花,那流光溢彩的漫天花火,便留在初一凌晨的祥和梦里。
大阳初一(醴人语)的乐趣,自然是和单位的同事先后聚伴,三五同群地走家串户,给领导和同事们拜年,得些好烟,一天弄他个几包十包,揣在兜里后小乐一回。
后来有了手机,我尤其做了小地方的文学“纤夫”之后,总要利用年节,理顺些关系,要发的短信和微信,总会让我“日理万机”,与文学与职事相关的领导和朋友频盈春贺,发与回乐此不疲。此外还得揪紧晨光,给文学群里的作家伙伴们发个红包,欣赏下自己长年与共的文友兄姊们的一大串回谢,生些幸福或叫陶醉的感觉。
初二日,自然要率家小给岳母拜年。岳家所处的泗汾是醴陵的南乡,风俗与东西北乡稍有不同。拜年饭通常有两碗鱼,其中一碗是不能吃的,大抵是“有余(鱼)有剩”的意思。我岳父是我从未见过的仙人,几十年我几乎没去上过坟头。我老家东富也地处东南乡,与江西萍乡的老关交界,给仙去的长辈“挂地”却几为定例。吃春饭也没那么多的讲究,桌上有的尽可吃去。醴陵北乡人做春饭讲究的是满碗堆尖,显示主人家待客的盛情,东南乡只要好吃却不嫌汤水,典型的南乡春饭则多是无汤少汤的干伙荤腥。
我曾打笑我的大姨夫:“到你们家没有菜吃。”
春饭会缺菜?自然笑他们饭桌上净是肉鱼,缺少蔬菜。其实荤腥贵于素菜,他家是实诚的要让亲戚吃好。
“初一崽,初二郎”,初一日的正题为给父母拜年,初二必去岳家,几乎是醴陵成年人携子女拜春的应有次序,鲜有例外。到了初三初四之后,却是春节娱乐的无序空间,亲友间互访互拜,请吃请玩,或麻将扑克,或卡拉0k,那就自由多了。
到了初六初七,醴陵人外出务工或在外地工作的人氏众多,多要交通出城,或火车,或私车,或飞机,每逢此一二日,常会一票难求,须得提前预订。苦就苦了疫情期间,北上广深与醴陵两地的行程非长,亲人间却要两头牵挂,不能团圆,甚至夫妻也无法相聚。
塞车是醴陵人春拜互动的桎梏。三十,初二和初七,是醴陵交通滞塞的高峰,车多人密,城里堵了城外堵,320和106国道是醴陵人外出回乡的主要节点,堵车则几乎司空见惯了。
初七初八休假结束,但好玩的人们却似乎尚未画上句号。有单位的人常要开个团拜会,拜年祝福的声音重又开锣。有一些人会组成舞狮长队,向工厂机关的人们舞狮贺年。如此余兴未消,到了正月十五吃完汤圆,年节才算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