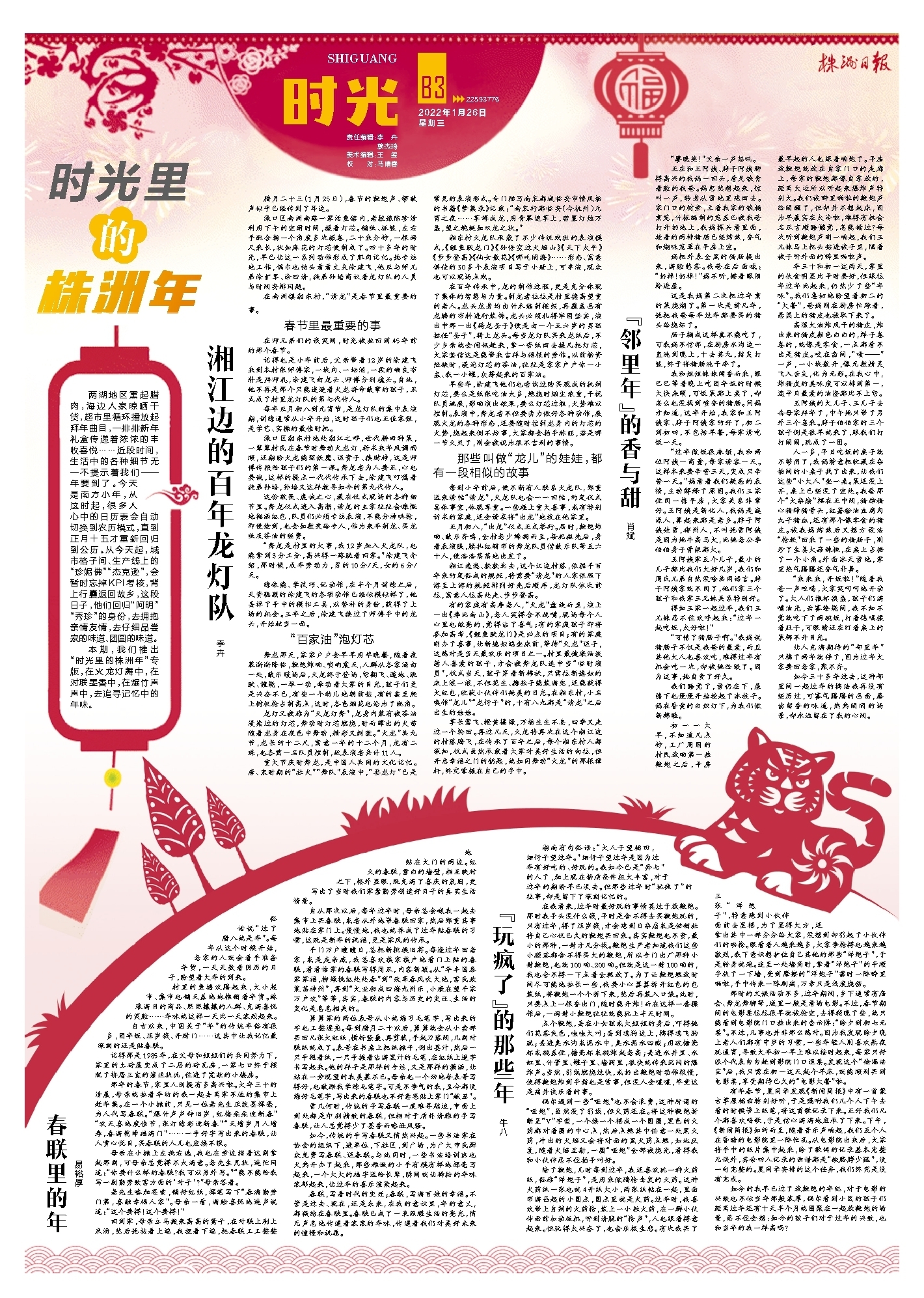“邻里年”的香与甜
“廖晚英!”父亲一声怒吼。
正在和王阿姨、胖子阿姨聊得高兴的我妈一回头,看见铁青着脸的我爸。妈忽然想起来,惊叫一声,转身从雪地里跑回去。家门口的树旁,立着我家的铁桶熏笼,竹板编制的笼盖已被我爸打开扔地上,我妈探头看里面,挂着的两排猪肠已经烤焦,香气和煳味笼罩在平房上空。
妈把外表全黑的猪肠提出来,满脸愁容。我爸在后面喊:“扔掉!扔掉!”妈不听,擦着眼泪拎进屋。
这是我妈第二次把过年熏的菜烧煳了。第一次是前几年,她把我爸每年过年都要买的猪头给烧坏了。
肠子糊成这样真不能吃了,可我妈不信邪,在厨房水沟边一直洗到晚上,十去其九,指尖打皱,终于将猪肠洗干净了。
我和姐姐妹妹闻香而来,眼巴巴等着晚上吃团年饭的时候大快朵颐,可饭菜都上桌了,却怎么也没找到喷香的猪肠。问妈才知道,这年开始,我家和王阿姨家、胖子阿姨家约好了,初二到初四,不包括早餐,每家请吃饭一天。
“过年做饭很麻烦,我和两位阿姨一商量,每家请客一天。这样本来要辛苦三天,变成只辛苦一天。”妈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主动解释了原因。我们三家住同一栋平房,大家关系非常好。王阿姨是新化人,我妈是涟源人,算起来都是老乡。胖子阿姨姓曾,郴州人,不叫她曾阿姨是因为她牛高马大,比她老公李伯伯身子骨架都大。
王阿姨家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都比我们大好几岁,我们和周氏兄弟自然没啥共同语言。胖子阿姨家就不同了,他们家三个孩子和我家三兄妹关系特别好。
得知三家一起过年,我们三兄妹忍不住欢呼起来:“过年一起吃饭,太好啦!”
“可惜了猪肠子啊。”我妈说猪肠子不仅是我爸的最爱,而且其他大人也喜欢吃,难得过年有机会吃一次,却被她给毁了。因为这事,她自责了好久。
我们睡觉了,雪仍在下,屋檐下也慢慢开始挂起了冰柱子。妈在昏黄的白炽灯下,为我们做新棉鞋。
初一一大早,不知道几点钟,工厂周围的村民放响第一挂鞭炮之后,平房最早起的人也跟着响炮了。平房放鞭炮就放在自家门口的走廊上,每家的鞭炮都像自家放的,距离太近所以听起来爆炸声特别大。我们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给闹醒了,但却并不想起床,因为早晨实在太冷啦,难得有机会名正言顺睡懒觉,怎能错过?每次听到鞭炮声刚一响起,我们三兄妹马上把头钻进被子里,隔着被子听外面的噼里啪啦声。
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家里的伙食明显比平时要好,但跟往年过年比起来,仍然少了些“年味”。我们急切地盼望着初二的“大餐”,爸妈则在厨房忙碌着,悬梁上的猪皮也被取下来了。
高温大油炸风干的猪皮,炸出来的猪皮颜色白白的,样子卷卷的,就像是零食,一点都看不出是猪皮。咬在齿间,“嗤——”一声,一小块散开,像无数精灵飞入舌尖,化为无形。在我心中,炸猪皮的美味度可以排到第一,连平日最爱的油渣都比不上它。
王阿姨的大儿子、三儿子去岳母家拜年了,中午她只带了另外三个崽来。胖子伯伯家的三个孩子倒是很早就来了,跟我们打打闹闹,玩成了一团。
人一多,平日吃饭的桌子就不够用了,我妈特意把收藏在杂物间的小桌子找了出来,让我们这些“小大人”坐一桌。菜还没上齐,桌上已经没了空处。我爸那个“大杂烩”摆在正中间,猪肺猪心猪蹄猪骨头,红薯粉油豆腐肉丸子猪血,还有那个像零食的猪皮。被我妈烤焦后又想方设法“抢救”回来了一些的猪肠子,则炒了生姜大蒜辣椒,在桌上占据了一个小角。外面冰天雪地,家里热气腾腾还香气扑鼻。
“来来来,开饭啦!”随着我爸一声吆喝,大家笑呵呵地开动了。大人们推杯换盏,孩子们满嘴油光,云雾缭绕间,我不知不觉就吃下了两碗饭,打着饱嗝揉着肚子,可眼睛还在盯着桌上的菜挪不开目光。
让人充满期待的“邻里年”只搞了两年就停了,因为过年大家要回老家,聚不齐。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这种邻里间一起过年的搞法我再没有经历过,可雾气腾腾的画面,唇齿留香的味道,热热闹闹的场景,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