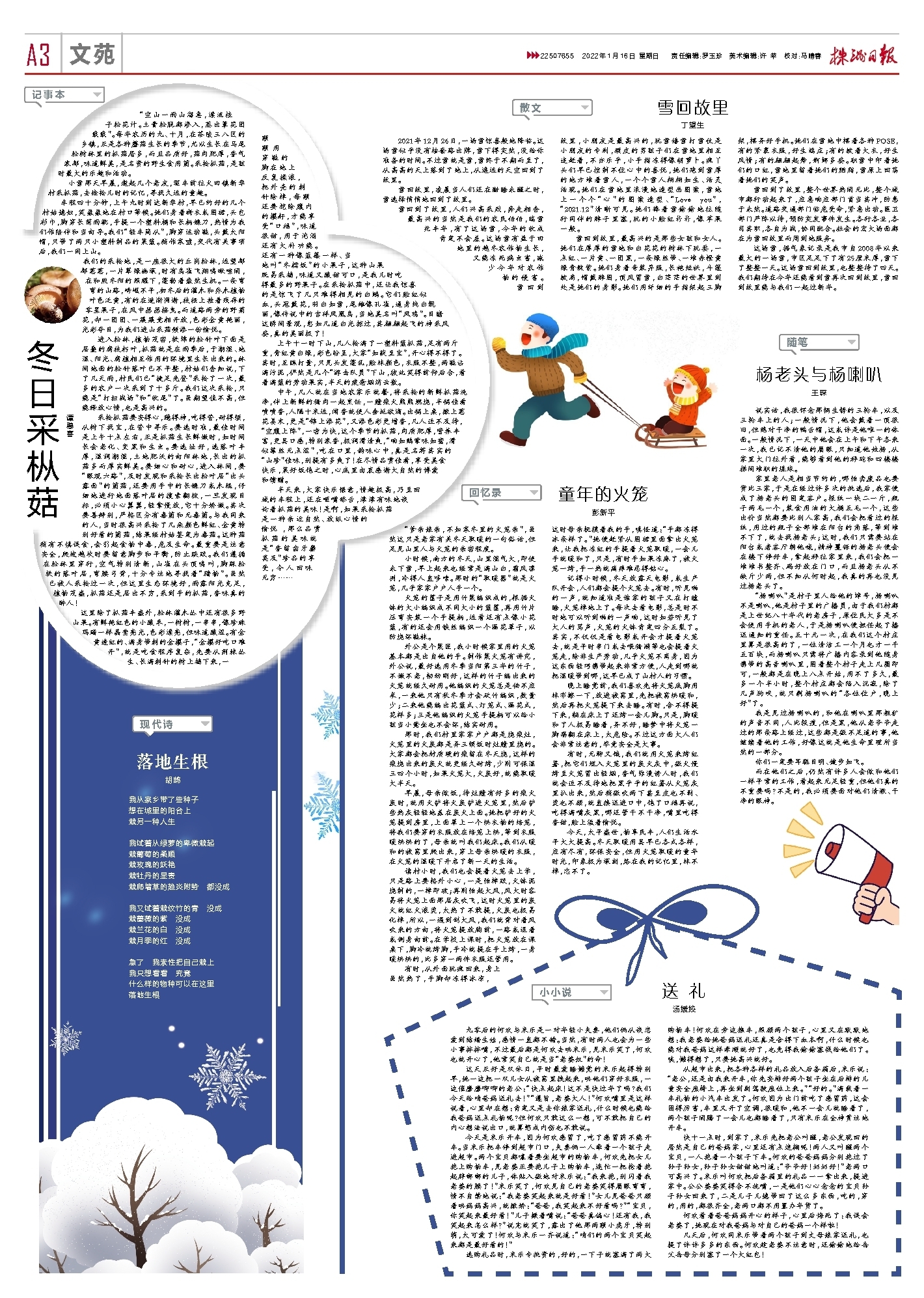杨老头与杨喇叭
王琛
说实话,我很怀念那辆生锈的三轮车,以及三轮车上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会戴着一顶很旧,但绝对干净的鸭舌帽,这或许是他唯一的体面。一般情况下,一天中他会在上午和下午各来一次,我已记不清他的眉眼,只知道他姓杨,从家里大门往外看,能够看到他的秤砣和四楼楼梯间堆积的煤球。
家里老人是相当节约的,哪怕卖废品也要货比三家,于是在经过许多次的挑选后,我家便成了杨老头的固定客户。报纸一块二一斤,瓶子两毛一个,装食用油的大桶五毛一个,这些出价当然都要比别人家高,我们会把看过的报纸,用过的瓶子全部堆在阳台的角落,等到堆不下了,就去找杨老头;这时,我们只需要站在阳台或者客厅朝他喊,精神矍铄的杨老头便会在楼下停好车,拿起秤往家里来,我们会把一堆堆书整齐、码好放在门口,而且杨老头从不缺斤少两,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真的再也没见过杨老头了。
“杨喇叭”是村子里人给他的绰号,杨喇叭不是喇叭,他是村子里的广播员,由于我们村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原住民大多是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于是杨喇叭便担任起了播送通知的重任。五十元一次,在我们这个村庄里算是很高的了,一位清洁工一个月也才一千五百块,而杨喇叭只需将广播内容录到他随身携带的高音喇叭里,围着整个村子走上几圈即可,一般都是在晚上八点开始,用不了多久,最多一个半小时,整个村庄都会陷入沉寂,除了几声狗吠,就只剩杨喇叭的“各位住户,晚上好”了。
我是见过杨喇叭的,和他在喇叭里那粗犷的声音不同,人比较瘦,但是黑,他从老爷爷走过的那条路上经过,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他继续着他的工作,好像这就是他生命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你们一定要耳聪目明、健步如飞。
而在他们之后,仍然有许多人会做和他们一样平常的工作,看起来无足轻重,但他们真的不重要吗?不是的,我必须要面对他们清澈、干净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