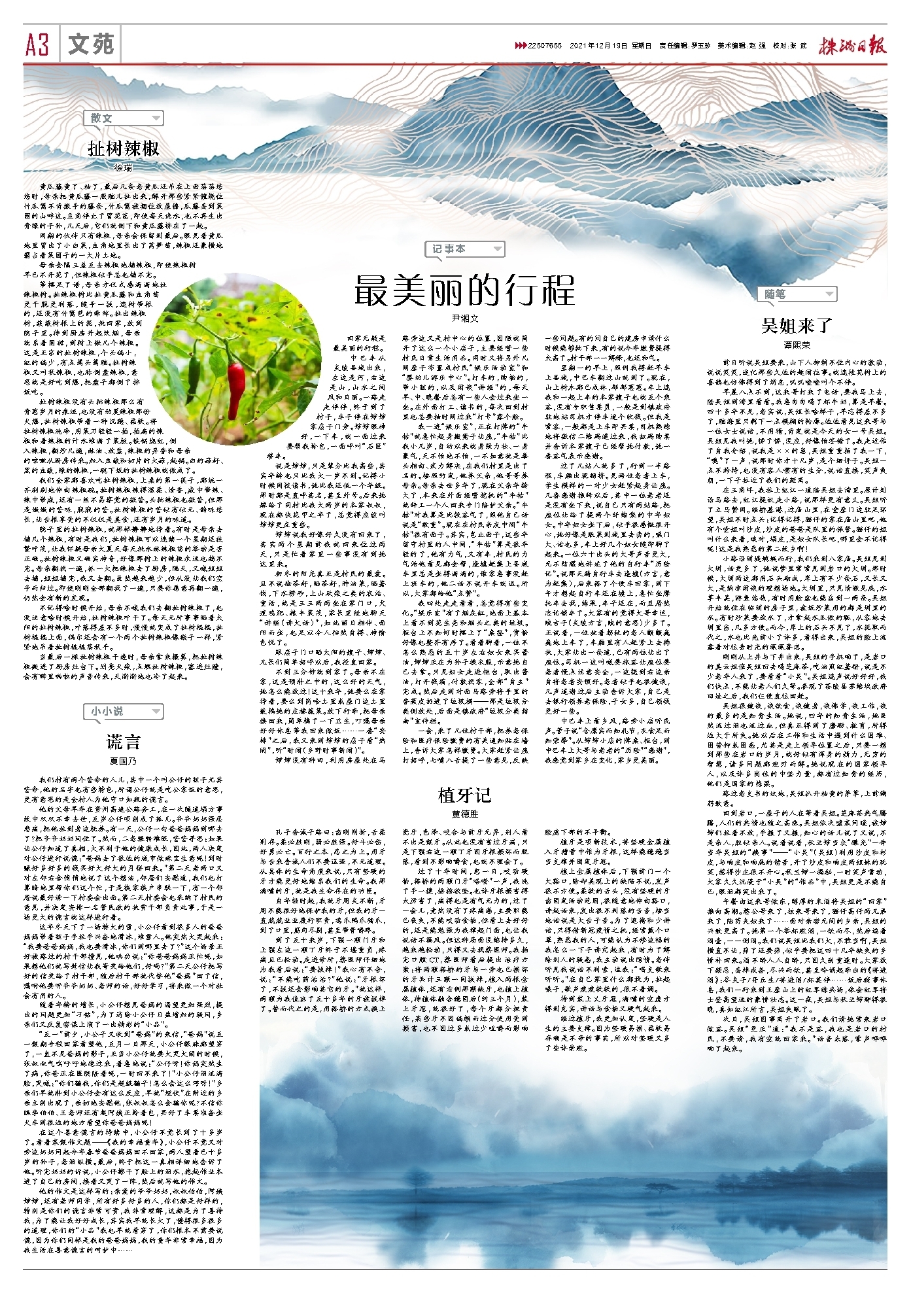吴姐来了
谭熙荣
前日听说吴姐要来,山下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说笑笑,追忆那些久远的趣闻往事。就连桂花树上的喜鹊也仿佛得到了消息,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早晨八点不到,这来哥打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去,陪吴姐到湾里看看。我急匆匆喝了杯牛奶,算是早餐。四十多年不见,老实说,吴姐长啥样子,早忘得差不多了,脑海里只剩下一点模糊的轮廓。远远看见这来哥与一位女士说话,不用猜,肯定就是今天的女一号吴姐。吴姐见我叫她,愣了愣,没应,好像怕答错了。我走近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是××的崽,吴姐重重拍了我一下,“噢”了一声,说那时你才十几岁,是个细伢子。吴姐一点不矜持,也没有客人惯有的生分,说话直接,笑声爽朗,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在三角坪,我拉上红江一道陪吴姐去湾里。原计划沿马路去,红江提议走小路,说那样更有意义。吴姐听了立马赞同。经桥基港,过庙山里,在堂屋门边驻足环望,吴姐不时点头:记得记得,猫仔的家在庙山里吧,他有个堂姐叫沙皮,沙皮的爸爸是队里的保管。猫仔的姐叫什么来着,哦对,塌皮,是妇女队长吧,哪里会不记得呢!这是我熟悉的第二故乡啊!
小路沿圳堤蜿蜒而行,我们来到八家庙。吴姐见到大圳,话更多了,她说梦里常常见到岩口的大圳。那时候,大圳两边都用石头砌成,岸上有不少条石,又长又大,是纳凉闲谈的理想场地。大圳里,只见清澈见底,水草丰美,游鱼悠哉,有时用脸盆也能舀到一两条。吴姐开始就住在临圳的房子里,煮饭炒菜用的都是圳里的水。有时炒菜要放水了,才拿起水瓜做的瓢,从容地去圳里舀,几多方便。而今,岸上的石头不见了,水泥取而代之,水也比先前小了许多,看得出来,吴姐的脸上流露着对往昔时光的深深眷恋。
刚刚从上井与下井出来,吴姐的手机响了,是岩口的美云姐催吴姐回去喝芝麻茶,吃油煎红薯饼,说是不少老年人来了,要看看“小吴”。吴姐连声说好好好,我们快点,不能让老人们久等。参观了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之后,我们仨便直往回赶。
吴姐很健谈,谈饮食,谈健身,谈佛学,谈工作,谈的最多的是知青生活。她说,四年的知青生活,她虽然流过泪也流过血,但真正得到了磨砺、教育,所得远大于所失。她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困苦抑或困惑,尤其是走上领导位置之后,只要一想到那些在岩口的岁月,就好似有浑身的精力,无穷的智慧,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她说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岗位的中坚力量,都有过知青的经历,他们是国家的栋梁。
路过老支书的坟地,吴姐扒开枯黄的茅草,上前鞠躬致意。
回到岩口,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吴姐。芝麻茶热气腾腾,人们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吴姐依次嘘寒问暖,被婶婶们拉着不放,手握了又握,知心的话儿说了又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说着说着,秋兰婶当众“曝光”一件当年吴姐的“糗事”——“小吴”(吴姐)利用沙皮和杉皮,与响皮和响屁的谐音,开了沙皮和响皮两姐妹的玩笑,惹得沙皮很不开心。秋兰婶一揭秘,一时笑声雷动,大家久久沉浸于“小吴”的“作品”中,吴姐更是不能自已,眼泪都笑出来了。
午餐由这来哥做东,醇厚的米酒将吴姐的“回家”推向高潮。憨公哥来了,核来哥来了,猫仔高仔两兄弟来了,陆苟夫妇来了……面对亲密无间的乡亲,吴姐的兴致更高了。她第一个举杯敬酒,一饮而尽,然后端着酒壶,一一倒酒。我们说吴姐比我们大,不敢当啊,吴姐横直不让,筛了还要筛,似乎要把这四十几年缺失的乡情补回来。酒不醉人人自醉,只因久别重逢时。大家放下顾忌,丢掉戒备,尽兴而饮,甚至吟诵起李白的《将进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饭后稍事休息,我们一行来到王屋山上的红军练兵场,体会红军将士登高望远的豪情壮志。这一夜,吴姐与秋兰婶聊得很晚,真如红江所言,吴姐失眠了。
次日,吴姐因事离开了岩口。我们请她常来岩口做客。吴姐“更正”道:“我不是客,我也是岩口的村民,不要请,我有空就回家来。”话音未落,掌声哗哗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