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茶陵谈《文学虚构艺术》

讲座结束后,当地文学爱好者手拿新书《喊山应》,排队等待王跃文老师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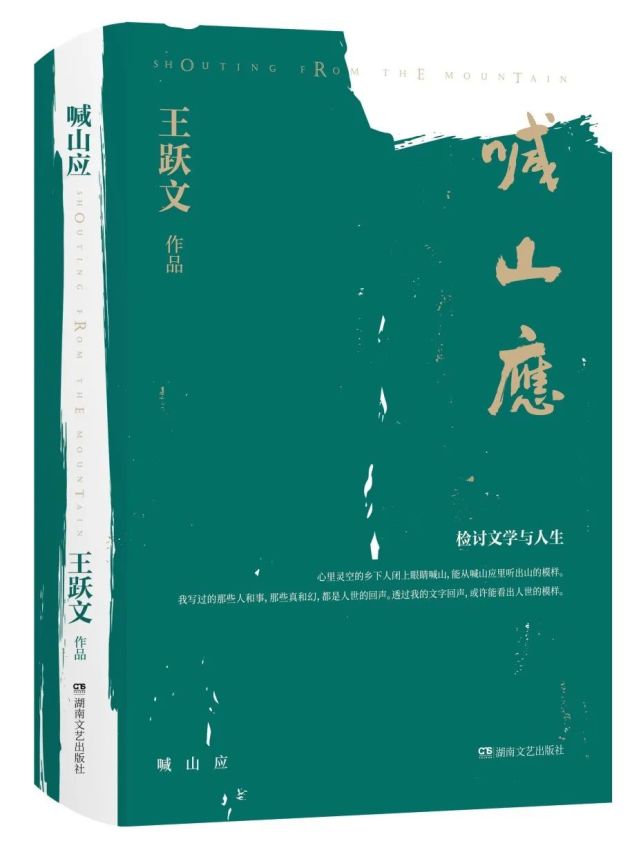
王跃文新书《喊山应》书封

王跃文讲课现场
郭 亮
“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涧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我写过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作品集《喊山应》中,著名作家、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以这样的方式来回顾、检讨自己三十余年的文字之路,中国社会这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也在书中以独特的视角呈现。
11月27日上午,茶陵县严塘镇和吕石峰仙森林康养基地,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学写作队伍建设,提高基层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水平,繁荣和发展基层文化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基地所在的中国花湖谷景区成功申报为湖南省文学创作示范基地,当日举行正式签约授牌仪式,包括王跃文在内的省市两级文联领导、嘉宾及茶陵当地领导并数十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当日的签约授牌仪式。
仪式之后,王跃文做了名为《文学虚构艺术》的主题讲座,结合其多年文学创作的心得,讲述了文学虚构的现实依据、逻辑依据、心理依据等内容,以及文学创作中应如何把握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分寸限度。
虚构有时候比真实还真
虚构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想象,都是虚构。因为虚构,有了我们人类最早对宇宙的认识;也因为虚构,有了文学,有了艺术,有了哲学,有了宗教。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却喜欢读各种宗教的书籍。比如说基督教的《圣经》,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在我这样一个非基督徒看来,《圣经>里的这个故事就是最早的文学虚构。
虚构作为一种文学手法,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手法。以文体而论,我们知道,写散文可以虚构,也可以不虚构;写诗歌可以虚构,也可以不虚构;写报告文学,原则上不准虚构,但是,写小说一定要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但是,虚构,不等于虚假,在我看来。虚构的真实有时候比客观的真实还要真实,因为它是一种本质上的真实。
我也经常碰到有些朋友拿自己写的小说给我看,让我提一些意见。这些朋友往往会拍着胸脯说,王老师,我这个小说就是按照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把它写下来,一丝假都没有。我会告诉他,你这个小说给人感觉不真实,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你原原本本写下来,没有虚构的情节。打个比方,生活中很多的极端场景,也有很多的离奇古怪,但是,如果一个小说里面全是这种离奇古怪,全是这种极端和巧合,你说会真实吗?真实肯定是真实的,但是人们读了以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他不是生活的日常。再举个例子,有一个诗人,写在当年的极端岁月里,有一个人实在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折磨,就在自己家的门背后上吊自杀了。这个诗人写,秋风吹着那扇门,哐当哐当响。这个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不真实的,因为一扇门后面挂着一具上吊去世的人的遗体的话,如果不是狂风,这个门一般的风是吹不动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诗句特别好,因为他涉及一个本质的哲学,就是说在那种特殊的、严酷的极端环境中,有些人的生命是没有重量的。
那么,什么是虚构呢?我们去翻汉语词典,解释是凭想象造出来,很简单的一个定义。但是。作为文学创作的虚构,我觉得这种解释还过于简单。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谈到写境和造境的问题,“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临近于理想故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诗人,他造的境,非常地逼近自然,又同理想密切相关。所以说,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写小说也好,写其他任何东西也好,凡是跟人相关的,包括人的思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之类,都是虚构,或者说,都有虚构。
近些年流行一个概念,叫非虚构文学,其实以前也有,叫纪实文学,或者说报告文学,我经常问他们,这三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我看来,所谓的非虚构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都是一回事,都是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某件事做文学化的描述。那么,这些文学作品中有没有虚构呢?我觉得是有的,这些虚构也无损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表达。
遵循艺术规律的虚构
我们一定要清楚,虚构不等于胡编乱造,一定要遵循某种艺术规律。
一是现实依据。现实生活是我们进行文学虚构最基础的依据,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很多朋友说我的小说特别真实,还有人对号入座,说这个写的是谁,那个又是谁,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所有的对号入座都是自作多情。之所以让人有对号入座的错觉,无非映射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让我们有感同身受之共情。再如历史小说的创作,像我写《大清相国》,阅读了大量的清史资料,既有正史,也有野史,从顺治朝到康熙朝,这七十多年发生过的大事,我都是一天天看过来的,书里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有史可稽的,尽管为了小说的故事性,我在书中虚构了大量的细节,但都是基于这些史料给我的现实依据。再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特别荒诞不经的寓言式小说写法,可也有其现实依据,即我们人性中共有的善恶道德观的一体两面。
二是文化依据。我们的古典小说,《西游记》里写仙界、人间、地狱,对应的是天地人三才,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红楼梦》里写大荒山、无稽崖、太虚幻境,还有什么补天孑遗的一块顽石之类,也是自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而来。再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采访时说过,“我要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我们回看《百年孤独》,尽管批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但其精神内核还是童年马尔克斯眼中一个家族的起伏兴衰、爱恨荣辱。马尔克斯极推崇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马拉莫》,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在母亲逝世后返回家乡寻找父亲的故事,在家乡,他遇到的所有人都是亡魂,通过跟那些亡魂的交谈,了解到自己父亲的一生......看过电影《寻梦环游记》的都知道,这是典型的墨西哥亡灵节作为其文化依据的。
三是逻辑依据。创作要讲逻辑,不管用什么手法,一定要把逻辑理顺。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金农续诗的例子,说的是富绅某请客,邀约金农等一批文人陪客,席间行酒令,富绅糊里糊涂来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气氛一时很尴尬,因为柳絮是白色的嘛,怎么能片片红呢?这个时候,金农就站出来了,说东家这诗其实是元朝某个诗人写的,那个诗人不是很有名,所以也流传不广,原诗其实是“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这样一来,逻辑便通了,夕阳一照,柳絮自然便是红的了。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写建桥的时候,有河妖作怪,白天建,晚上就塌了,后面为了镇压河妖,把一个小孩子砌到桥墩里面,孩子的母亲因为思念自己的孩子发疯了,每天都跑到桥墩下面,冲着桥墩上的一个小孔洞喂奶。自此以后,那个孔洞便能流出白色的乳汁,400余年来,一直如此。这样的叙事逻辑放在现代科技未曾萌芽的古代没问题,可伊沃·安德里奇是现代作家,生活在科技昌明的近现代,这样的逻辑显然行不通。所以,作家在书里也做出了解释,所谓的河妖作怪,只是反对建桥的人在夜里搞破坏,而孔洞中流出乳汁,是因为,砌桥的石头中含有石灰,水流冲过,发生反应,自然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这样一来,逻辑也就理顺了。
四是心理依据。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大家都熟悉,里面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主人公格里高利总能听到顿河的咆哮,不管是在他劳作还是休息的时候,乃至后来成为军人,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也可以听到这种咆哮声。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也可以说是肖洛霍夫的虚构,可我们并不觉得这种虚构突兀,顿河两边的土地是哥萨克人祖祖辈辈用鲜血浇灌出来的,主人公格里高利是个典型的哥萨克人,却被大时代裹挟,在白军、红军之间犹豫不决,最后还成为了土匪,而他的家人,爷爷、爸爸、妈妈、哥哥、嫂嫂、妹妹、女儿,还有他最爱的情妇阿克西妮亚,都死掉了,小说的结尾如此写道,“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着的东西。”再联想到格里高利耳边不时回响的顿河的咆哮,虽是虚构,却正是格里高利对顿河以及顿河两岸的土地深深的情感最为强大的心理依据。
五是美学经验依据。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就文体来说,每个时代的文学样式都是不断变化的。民国著名学人章太炎,学问极好,但是他发誓不作诗,为什么呢?因为前人写的好诗太多了,以章太炎的学术水平,对诗的格律的理解,要写诗,信手拈来,但要出新,很难。所以呢,干脆一辈子不写诗。具体到小说,举个例子,《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空放在同一句话里交代清楚,很多作家都模仿过这个开头,包括我很尊敬的陈忠实先生,《白鹿原》的开头也是这样典型的将三个时空融在一句话里面。那么,这个句式是哪儿来的呢,后面我看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马拉莫》,在这部小说的大约3/4篇幅处,出现了这么一个类似的句式。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要多借鉴学习,同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要带着问题去多思考,汲取经验,而又不全盘照搬,扬长避短地去创作。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新疆作家刘亮程早两年出了部长篇小说《捎话》,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手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童话、寓言、神话、志怪、荒诞,卡通、蒙太奇、电影、小说、散文、诗歌,可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并不突兀,都统一在作者构建的宇宙观之下,呈现出独有的迷人的文学镜像,这是将美学经验依据玩到极致的虚构。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王跃文先生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