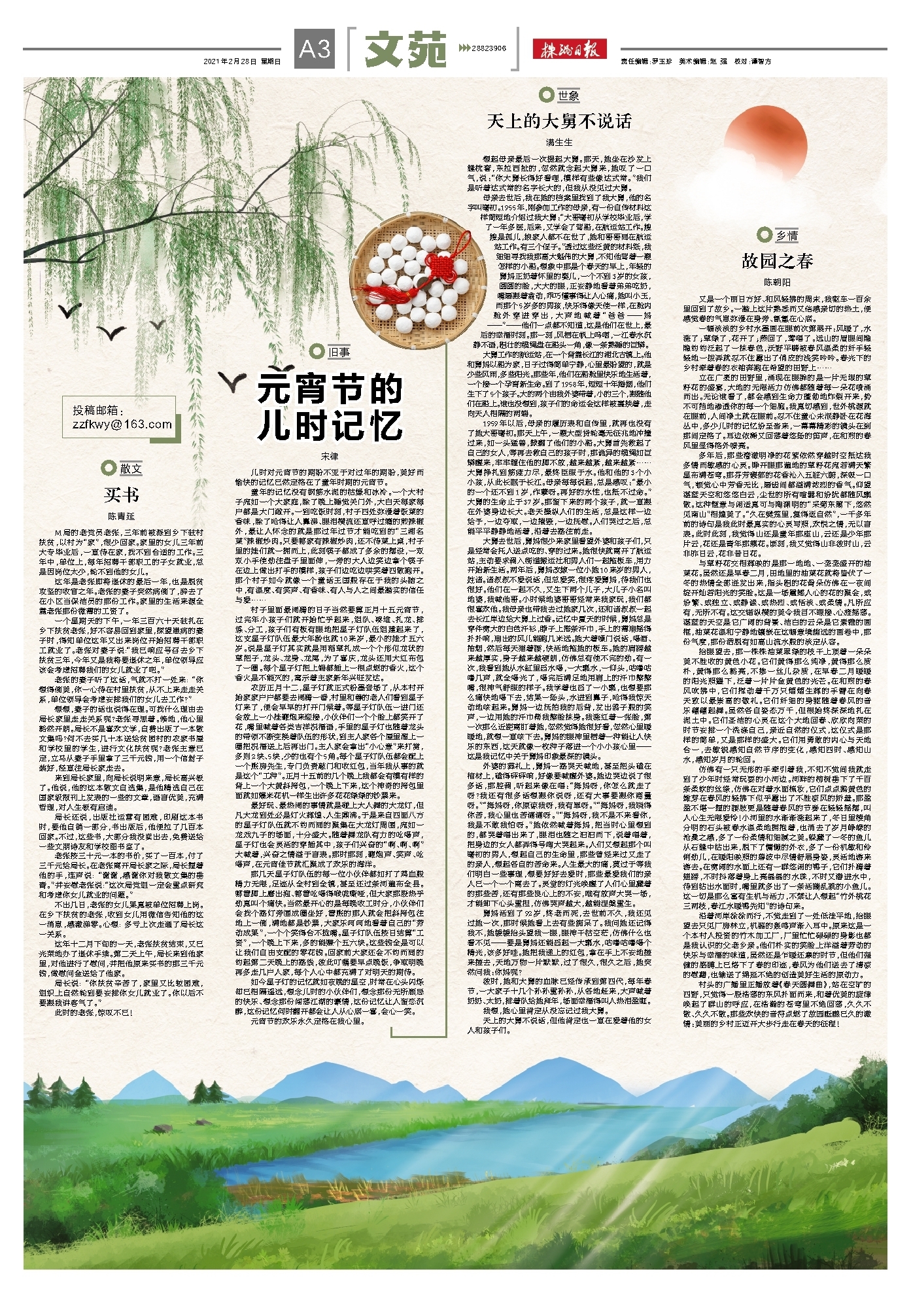天上的大舅不说话
想起母亲最后一次提起大舅。那天,她坐在沙发上缝枕套,东拉西扯的,忽然就念起大舅来,她叹了一口气,说:“你大舅长得好看哩,模样有些像达式常。”我们是听着达式常的名字长大的,但我从没见过大舅。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档案里找到了我大舅,他的名字叫曙初。1955年,刚参加工作的母亲,有一份自传材料这样简短地介绍过我大舅:“大哥曙初从学校毕业后,学了一年多医,后来,又学会了驾船,在航运站工作。嫂嫂是孤儿,娘家人都不在世了,她和哥哥同在航运站工作。有三个侄子。”透过这些泛黄的材料纸,我细细寻找我那高大魁伟的大舅,不知他驾着一艘怎样的小船。想象中那是个春天的早上,年轻的舅妈正奶着怀里的婴儿,一个不到3岁的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正安静地看着弟弟吃奶,嘴唇跟着翕动,乖巧懂事得让人心痛,她叫小玉,而那个5岁多的男孩,快乐得像天使一样,在舱内舱外穿进穿出,大声地喊着“爸爸——妈——”——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他们在世上,最后的幸福时刻。那一刻,风栖在帆上呜咽,一江春水沉静不语,粗壮的缆绳盘在船头一角,像一条熟睡的巨蟒。
大舅工作的航运站,在一个背靠长江的湘北古镇上。他和舅妈以船为家,日子过得简单宁静,心里最盼望的,就是少些风雨,多些阳光。那些年,他们在船舱里快乐地生活着,一个接一个孕育新生命。到了1958年,短短十年婚姻,他们生下了5个孩子。大的两个由我外婆带着,小的三个,跟随他们在船上。谁也没想到,孩子们的命运会这样被裹挟着,走向天人相隔的两端。
1959年以后,母亲的履历表和自传里,就再也没有了她大哥曙初。那天上午,一艘大型货轮毫无征兆地冲撞过来,如一头猛兽,掀翻了他们的小船。大舅首先救起了自己的女人,等再去救自己的孩子时,那诡异的缆绳如巨蟒醒来,牢牢缠住他的脚不放,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大舅挣扎到筋疲力尽,最终臣服于水。他和他的3个小小孩,从此长眠于长江。母亲每每说起,总是感叹:“最小的一个还不到1岁,作孽呀。再好的水性,也抵不过命。”大舅的生命止于37岁。那留下来的两个孩子,就一直跟在外婆身边长大。老天操纵人们的生活,总是这样一边给予,一边夺取,一边摧毁,一边抚慰。人们哭过之后,总能平平静静地活着,沿着去路往前走。
大舅去世后,舅妈很少来家里看望外婆和孩子们,只是经常会托人送点吃的、穿的过来。她很快就离开了航运站,主动要求调入街道搬运社和男人们一起拖板车,用力开始新生活。两年后,舅妈改嫁一位小她10来岁的男人,姓诸。诸叔叔不爱说话,但总爱笑,很疼爱舅妈,待我们也很好。他们在一起不久,又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名叫地婆,我喊他哥。小时候地婆哥哥经常来我家玩,我们都很喜欢他。我母亲也带我去过她家几次,还和诸叔叔一起去长江岸边给大舅上过香。记忆中夏天的时候,舅妈总是穿件宽大的白色汗衫,脖子上搭条汗巾,手上的薄扇摇得扑扑响,扇出的风儿能跑几米远。她大着嗓门说话,喝酒、抽烟,然后每天猫着腰,快活地拖她的板车。她的肩膀越来越厚实,身子越来越硬朗,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劲。有一次,我看到她从水缸里舀水喝,一大瓢水,一仰头,咕噜咕噜几声,就全喝光了,喝完后满足地用肩上的汗巾擦擦嘴,很神气舒服的样子。我学着也舀了一小瓢,也想要那么痛快地喝下去,结果一扬头,水进到鼻子,呛得我惊天动地咳起来。舅妈一边抚拍我的后背,发出鸽子般的笑声,一边用她的汗巾帮我擦脸抹身。我涨红着一张脸,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盯着她,忽然觉得她很好看,忽然心里暖暖地,就想一直咳下去。舅妈的眼神里栖着一种能让人快乐的东西,这天就像一枚种子落进一个小小孩心里——这是我记忆中关于舅妈印象最深的镜头。
外婆的葬礼上,舅妈一路哭天喊地,甚至把头磕在棺材上,磕得砰砰响,好像要喊醒外婆。她边哭边说了很多话,那腔调,听起来像在唱:“姆妈呀,你怎么就走了呀?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呀,还有大事要跟你商量呀。”“姆妈呀,你原谅我呀,我有罪呀。”“姆妈呀,我晓得你苦,我心里也苦滴滴呀。”“姆妈呀,我不是不来看你,我是不敢我怕呀。”她依然喊着姆妈,把当时心里想到的,都哭着唱出来了,眼泪也随之汩汩而下,说着唱着,把身边的女人都弄得号啕大哭起来。人们又想起那个叫曙初的男人,想起自己的生命里,那些曾经来过又走了的亲人,想起各自的苦命来。人生最大的痛,莫过于等我们明白一些事理,想要好好去爱时,那些最爱我们的亲人已一个一个离去了。灵堂的灯光唤醒了人们心里藏着的那些苦,还有那些良心上的不安,唯有放声大哭一场,才能卸下心头重担,仿佛哭声越大,越能涅槃重生。
舅妈活到了92岁,终老而死,去世前不久,我还见过她一次,那时候她看上去有些痴呆了。我问她还记得我不,她缓缓抬头望我一眼,眼神干枯空茫,仿佛什么也看不见——要是舅妈还能舀起一大瓢水,咕噜咕噜喝个精光,该多好哇。她把我递上的红包,拿在手上不安地搓来搓去,天地万物一片默默,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她突然问我:你妈呢?
彼时,她和大舅的血脉已经传承到第四代,每年春节,一大家子十几个孙孙重孙孙,从各地赶来,大声喊着奶奶、太奶,排着队给她拜年,场面幸福得叫人热泪盈眶。
我想,她心里肯定从没忘记过我大舅。
天上的大舅不说话,但他肯定也一直在爱着他的女人和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