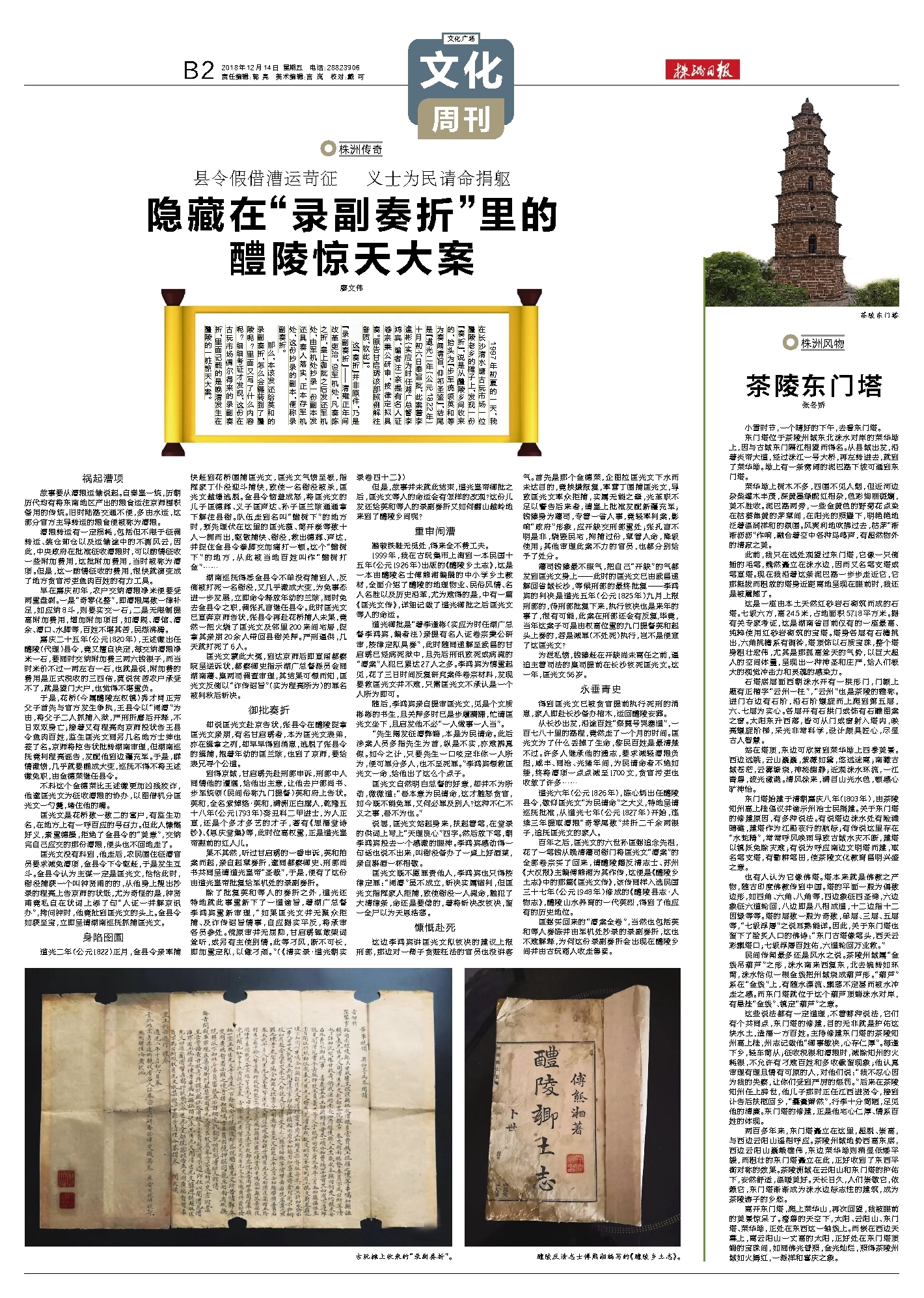隐藏在“录副奏折”里的 醴陵惊天大案
廖文伟
1997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长沙清水塘古玩市场一位醴陵老乡的摊子上,发现一份“奏折”,说是从醴陵乡间收来的,抬头为“步军统领英和等为奏闻请旨,仰祁圣鉴”,结尾是“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十月初六日奉旨批,此案着李逢彬(实应为时任湖广总督李鸿宾,编者注)亲提有名人证卷宗秉公研审,按律定拟具奏。原告甘启琇该部照例解往备质,钦此”。
这“奏折”并非原件,乃是“录副奏折”——清雍正年间改革吏治,设军机处,凡奏陈之折,皇上御批之后发还军机处,由军机处抄录一份副本发还具奏人落实,正本存军机处,这份抄录的副本,便称录副奏折。
那么,本该发还给英和的录副奏折,怎么会辗转到了醴陵呢?里面又写了什么内容呢?细细考证才发现,这份在古玩市场偶尔得来的录副奏折,里面记载的是晚清发生在醴陵的一桩惊天大案。
祸起漕项
故事要从漕粮运输说起。自秦皇一统,历朝历代均有将东南地区产出的粮食运往京师囤积备用的传统。旧时陆路交通不便,多由水运,这部分官方主导转运的粮食便被称为漕粮。
漕粮转运有一定损耗,包括但不限于征调转运、装仓卸仓以及运输途中的不测风云,因此,中央政府在批准征收漕粮时,可以酌情征收一些附加费用,这批附加费用,当时被称为漕项。但是,这一酌情征收的费用,很快就演变成了地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有力工具。
早在嘉庆初年,农户交纳漕粮净米便要受两重盘剥。一是“奇零化整”,即漕粮尾数一律补足,如应纳8斗,则要实交一石;二是无限制提高附加费用,增加附加项目,如漕规、漕馆、漕余、漕口、水脚等,百姓不堪其苦,民怨沸腾。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王述徽出任醴陵(代理)县令,竟又擅自决定,每交纳漕粮净米一石,要同时交纳附加费三两六钱银子,而当时米价不过一两左右一石,也就是说,附加费的费用是正式税收的三四倍,莫说贫苦农户承受不了,就是望门大户,也觉得不堪重负。
于是,花桥(今属醴陵左权镇)秀才肖正芳父子首先与官方发生争执,王县令以“闹漕”为由,将父子二人抓捕入狱,严刑折磨后开释,不日双双身亡;接着又有程亮向京师投状告王县令鱼肉百姓,监生匡光文同另几名地方士绅也签了名。京师将控告状批转湖南审理,但湖南巡抚竟判程亮诬告,发配他到边疆充军。于是,群情激愤,几乎就要酿成大变,巡抚不得不将王述徽免职,由金德荣继任县令。
不料这个金德荣比王述徽更加凶残狡诈,他邀匡光文为征收漕粮的协办,以图借机分匡光文一勺羹,堵住他的嘴。
匡光文是花桥数一数二的富户,有监生功名,在地方上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但此人慷慨好义,素重德操,拒绝了金县令的“美意”,交纳完自己应交的那份漕粮,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匡光文没有料到,他走后,农民围住征漕官员要求减免漕项,金县令下令驱赶,于是发生互斗。金县令认为主谋一定是匡光文,恰恰此时,衙役捕获一个叫钟贤甫的的,从他身上搜出抄录的程亮上告京师的状纸,尤为奇怪的是,钟贤甫竟私自在状词上添了句“人证一并解京讯办”,拷问钟时,他竟扯到匡光文的头上。金县令如获至宝,立即呈请湖南巡抚抓捕匡光文。
身陷囹圄
道光二年(公元1822)正月,金县令亲率捕快赶到花桥围捕匡光文,匡光文气愤至极,指挥家丁仆役迎斗捕快,致使一名衙役被杀,匡光文越墙逃脱。金县令恼羞成怒,将匡光文的儿子匡德辉、义子匡声达、孙子匡兰陔通通拿下解往县衙。队伍走到名叫“蜡树下”的地方时,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匡光藻、简开泰等数十人一拥而出,驱散捕快、衙役,救出德辉、声达,并捉住金县令拳脚交加痛打一顿。这个“蜡树下”的地方,从此被当地百姓叫作“蜡树打金”……
湖南巡抚得悉金县令不单没有捕到人,反倒被打死一名衙役,又几乎激成大变,为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立即命令释放年幼的兰陔,同时免去金县令之职,调张孔言继任县令。此时匡光文已直奔京师告状,张县令再赴花桥捕人未果,竟然一把火烧了匡光文及邻里200来间宅居,捉拿其亲朋20余人带回县衙关押。严刑逼供,几天就打死了6人。
匡光文蒙此大冤,到达京师后即直闯都察院呈送诉状,都察御史指示湖广总督派员会同湖南藩、臬两司调查审理,其结果可想而知,匡光文反倒以“诈传诏旨”(实为程亮所为)的罪名被判秋后斩决。
御批奏折
却说匡光文赴京告状,张县令在醴陵捉拿匡光文亲朋,有名甘启琇者,本为匡光文表弟,亦在缉拿之列,却早早得到消息,逃脱了张县令的缉捕,抱着年幼的匡兰陔,也到了京师,要给表兄寻个公道。
到得京城,甘启琇先赴刑部申诉,刑部中人同情他的遭遇,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户部尚书、步军统领(民间俗称九门提督)英和府上告状。英和,全名索绰络·英和,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癸丑科二甲进士,为人正直,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著有《思福堂诗钞》、《恩庆堂集》等,此时位高权重,正是道光皇帝跟前的红人儿。
果不其然,听过甘启琇的一番申诉,英和拍案而起,亲自起草奏折,邀同都察御史、刑部尚书共同呈请道光皇帝“圣裁”,于是,便有了这份由道光皇帝批复给军机处的录副奏折。
除了批复英和等人的奏折之外,道光还特地就此事重新下了一道谕旨,着湖广总督李鸿宾重新审理,“如果匡光文并无聚众拒捕、及诈传诏旨情事,自应据实平反,将承审各员参处。傥原审并无屈抑,甘启琇辄敢架词耸听,或另有主使别情。此等刁风,断不可长,即加重定拟,以儆刁顽。”(《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四十二》)
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道光皇帝御批之后,匡光文等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观?这份儿发还给英和等人的录副奏折又如何翻山越岭地来到了醴陵乡间呢?
重审闹漕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99年,我在古玩集市上淘到一本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出版的《醴陵乡土志》,这是一本由醴陵名士傅熊湘编撰的中小学乡土教材,全面介绍了醴陵的地理物业、民俗风情、名人名胜以及历史沿革,尤为难得的是,中有一篇《匡光文传》,详细记载了道光御批之后匡光文等人的命运。
道光御批是“着李逢彬(实应为时任湖广总督李鸿宾,编者注)亲提有名人证卷宗秉公研审,按律定拟具奏”,此时随同递解至武昌的甘启琇已经病死狱中,且先后刑讯致死或病毙的“漕案”人犯已累达27人之多。李鸿宾为慎重起见,花了三日时间反复研究案件卷宗材料,发现要救匡光文并不难,只需匡光文不承认是一个人所为即可。
随后,李鸿宾亲自提审匡光文,见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且关押多时已是步履蹒跚,忙请匡光文坐下,且启发他不必“一人做事一人当”。
“先生揭发征漕弊端,本是为民请命。此后涉案人员多指先生为首,纵是不实,亦难辨真假。如今之计,只要先生一口咬定非你一人所为,便可罪分多人,也不至死罪。”李鸿宾想救匡光文一命,给他出了这么个点子。
匡光文自然明白总督的好意,却并不为所动,微微道:“吾本意为民请命,这才触怒贪官,如今既不能免罪,又何必罪及别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吾不为也。”
说罢,匡光文站起身来,扶起管笔,在堂录的供词上写上“天理良心”四字。然后放下笔,朝李鸿宾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李鸿宾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叫衙役备办了一桌上好酒菜,亲自斟酒一杯相敬。
匡光文既不愿罪责他人,李鸿宾也只得按律定罪:“闹漕”虽不成立,斩决实属错判,但匡光文指挥家人拒捕,致使衙役一人毙命,触犯了大清律条,命还是要偿的,着将斩决改绞决,留一全尸以为天恩浩荡。
慷慨赴死
这边李鸿宾讲匡光文拟绞决的建议上报刑部,那边对一帮子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没讲客气。首先是那个金德荣,企图拉匡光文下水而未达目的,竟挟嫌报复,率营丁围捕匡光文,导致匡光文率众拒捕,实属无能之辈,光革职不足以警告后来者,请皇上批准发配新疆充军;钱臻身为藩司,专管一省人事,竟轻率判案,影响“政府”形象,应开缺交刑部重处;张孔言不明是非,烧毁民宅,拘捕过份,草菅人命,降级使用;其他审理此案不力的官员,也都分别给予了处分。
藩司钱臻最不服气,把自己“开缺”的气都发到匡光文身上——此时的匡光文已由武昌递解回省城长沙,等候刑部的最终批复——李鸿宾的判决是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九月上报刑部的,待刑部批复下来,执行绞决也是来年的事了,很有可能,此案在刑部还会有反复,毕竟,当年这案子可是由权高位重的九门提督英和起头上奏的,若是减罪(不处死)执行,岂不是便宜了这匡光文?
为泄私愤,钱臻赶在开缺尚未离任之前,逼迫主管司法的臬司提前在长沙绞死匡光文。这一年,匡光文56岁。
永垂青史
得到匡光文已被贪官提前执行死刑的消息,家人即赴长沙备办棺木,运回醴陵安葬。
从长沙出发,沿途百姓“祭奠号哭塞道”,一百七八十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月的时间。匡光文为了什么丢掉了生命,黎民百姓是最清楚不过。许多人继承他的遗志,要求减轻漕粮负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为民请命者不绝如缕,终将漕项一点点减至1700文,贪官污吏也收敛了许多……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陈心炳出任醴陵县令,敬仰匡光文“为民请命”之大义,特地呈请巡抚批准,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开始,连续三年提取漕粮“奇零尾数”共折二千余两银子,追抚匡光文的家人。
百年之后,匡光文的六世孙匡弼追念先祖,花了一笔钱从晚清藩司衙门将匡光文“漕案”的全部卷宗买了回来,请醴陵籍反清志士、苏州《大汉报》主编傅熊湘为其作传,这便是《醴陵乡土志》中的那篇《匡光文传》,该传同样入选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修成的《醴陵县志·人物志》,醴陵山水养育的一代英烈,得到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匡弼买回来的“漕案全卷”,当然也包括英和等人奏陈并由军机处抄录的录副奏折,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这份录副奏折会出现在醴陵乡间并由古玩商人收走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