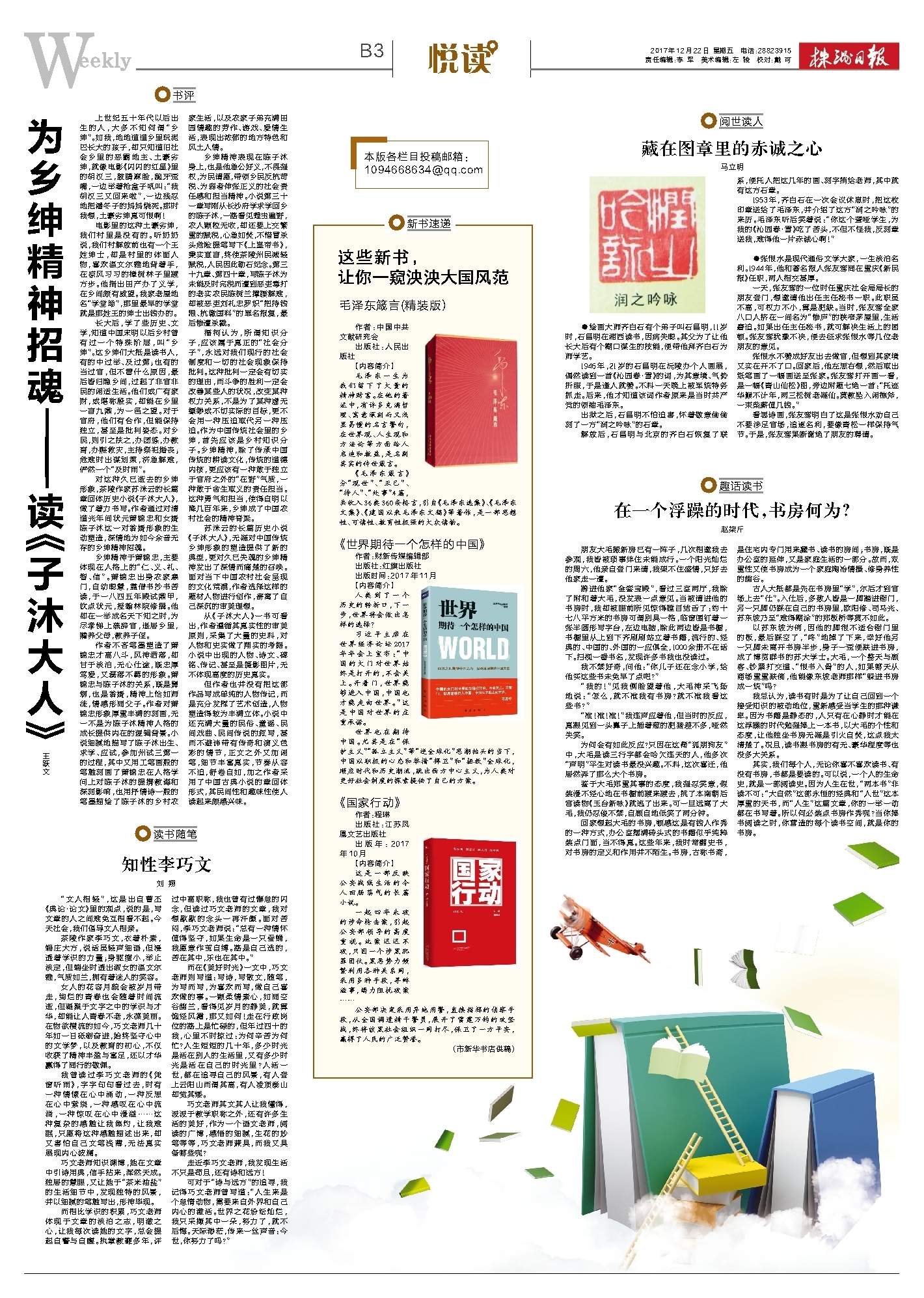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书房何为?
赵柒斤
朋友大毛搬新房已有一阵子,几次相邀我去参观,我皆被琐事绊住未能成行。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他亲自登门来请,我架不住盛情,只好去他家走一遭。
跨进他家“金銮宝殿”,看过三室两厅,我除了附和着大毛,没发表一点意见。当被请进他的书房时,我却被眼前所见惊得瞠目结舌了:约十七八平方米的书房可谓别具一格,临窗围钉着一张半圆形写字台,左边电脑,除此两边皆是书橱,书橱里从上到下齐刷刷站立着书籍,流行的、经典的、中国的、外国的一应俱全,1000余册不在话下。扫视一番书名,发现许多书我也没读过。
我不禁好奇,问他:“你儿子还在念小学,给他买这些书未免早了点吧?”
“我的!”见我侧脸望着他,大毛神采飞扬地说:“怎么,就不准我有书房?就不准我看这些书?”
“准!准!准!”我连声应着他,但当时的反应,真跟见到一头鼻子上插着葱的肥猪差不多,哑然失笑。
为何会有如此反应?只因在这帮“狐朋狗友”中,大毛是读三行字都会哈欠连天的人,他多次“声明”平生对读书最没兴趣。不料,这次喜迁,他居然弄了那么大个书房。
鉴于大毛郑重其事的态度,我强忍笑意,假装漫不经心地在书橱前踱来踱去,挑了本南朝后宫读物《玉台新咏》就逃了出来。可一旦远离了大毛,我仍忍俊不禁,自顾自地低笑了两分钟。
回家想起大毛的书房,顿感这是有钱人作秀的一种方式,办公室摆满砖头式的书籍似乎纯粹装点门面,当不得真。这些年来,我时常翻史书,对书房的定义和作用并不陌生。书房,古称书斋,是住宅内专门用来藏书、读书的房间;书房,既是办公室的延伸,又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故而,双重性又使书房成为一个家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幽谷。
古人大抵都是先在书房里“学”,尔后才到官场上去“仕”。入仕后,多数人皆是一脚踏进衙门,另一只脚仍踩在自己的书房里,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乃至“难得糊涂”的郑板桥等莫不如此。
以苏东坡为例,因他的脚很不适合衙门里的板,最后踩空了,“咚”地掉了下来,幸好他另一只脚未离开书房半步,身子一歪便跌进书房,成了博览群书的苏大学士。大毛,一个整天与顾客、钞票打交道、“恨书入骨”的人,如果哪天从商场重重跌倒,他能像东坡老师那样“躲进书房成一统”吗?
我总认为,读书有时是为了让自己回到一个接受知识的被动地位,重新感受当学生的那种谦卑。因为书籍是静态的,人只有在心静时才能在这浮躁的时代勉强捧上一本书,以大毛的个性和态度,让他独坐书房无疑是引火自焚,这点我太清楚了。况且,读书跟书房的有无、豪华程度等也没多大关系。
其实,我们每个人,无论你喜不喜欢读书、有没有书房,书都是要读的。可以说,一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一部阅读史。因为人生在世,“两本书”非读不可:“大自然”这部永恒的经典和“人世”这本厚重的天书,而“人生”这篇文章,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书写着。所以何必装点书房作秀呢?当你捧书阅读之时,你营造的每个读书空间,就是你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