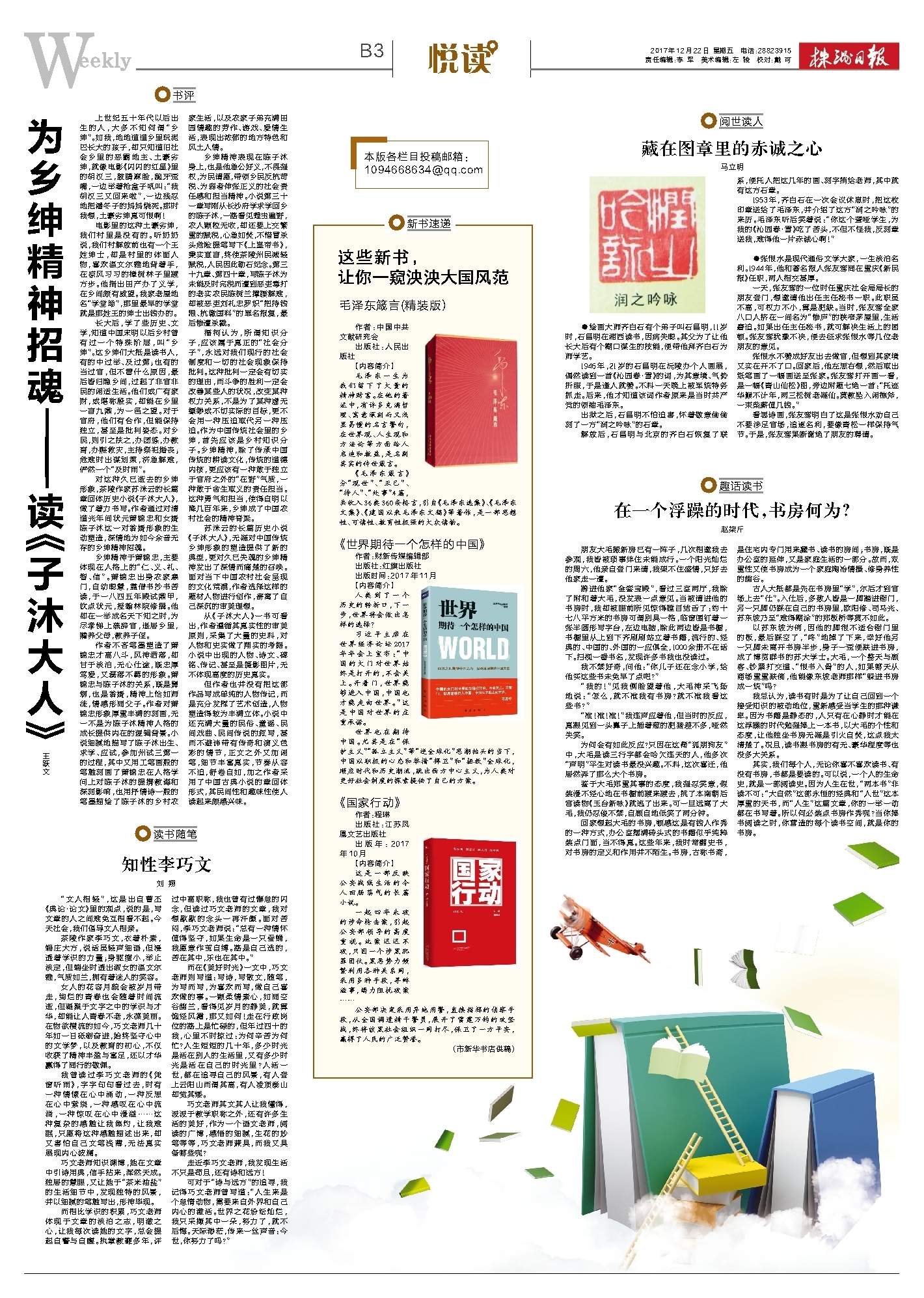书评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多不知何谓“乡绅”。如我,地地道道乡里玩泥巴长大的孩子,却只知道旧社会乡里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鼓睛麻脸,龅牙歪嘴,一边举着枪盒子吼叫:“我胡汉三又回来啦”,一边残忍地把潘冬子的妈妈烧死。那时我想,土豪劣绅真可恨啊!
电影里的这种土豪劣绅,我们村里是没有的。听奶奶说,我们村解放前也有一个王姓绅士,却是村里的体面人物,喜欢温文尔雅地背着手,在凉风习习的樟树林子里踱方步。他捐出田产办了义学,在乡间颇有威望。我家老屋地名“学堂坳”,那里最早的学堂就是那姓王的绅士出钱办的。
长大后,学了些历史、文学,知道中国宋明以后乡村曾有过一个特殊阶层,叫“乡绅”。这乡绅们大抵是读书人,有的中过举、及过第;也有的当过官,但不管什么原因,最后皆归隐乡间,过起了非官非民的闲适生活。他们或广有家财,或堪称殷实,却能在乡里一言九鼎,为一邑之望。对于官府,他们有合作,但能保持独立,甚至是批判姿态。对乡民,则引之扶之,办团练,办教育,办赈救灾,主持祭祀婚丧;危难时出谋划策,济急解难,俨然一个“及时雨”。
对这种久已逝去的乡绅形象,茶陵作家苏洣云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子沐大人》,做了着力书写。作者通过对清道光年间状元萧锦忠和女婿陈子沐这一对翁婿形象的生动塑造,深情地为如今余音无存的乡绅精神招魂。
乡绅精神于萧锦忠,主要体现在人格上的“仁、义、礼、智、信”。萧锦忠出身农家寒门,自幼聪慧,靠借书抄书苦读,于一八四五年殿试鼎甲,钦点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却在一举成名天下知之时,为尽孝悌上疏辞官,退居乡里,赡养父母,教养子侄。
作者不吝笔墨塑造了萧锦忠才高八斗,风神洒落,却甘于淡泊,无心仕途,既忠厚笃爱,又磊落不羁的形象。萧锦忠与陈子沐的关系,既是舅甥,也是翁婿,精神上恰如师徒,情感形同父子。作者对萧锦忠形象厚重丰满的刻画,无一不是为陈子沐精神人格的成长提供内在的逻辑背景。小说细腻地描写了陈子沐出生、求学、应试,参加州试三第一的过程,其中又用工笔画般的笔触刻画了萧锦忠在人格学问上对陈子沐的提携教诲和深刻影响,也用抒情诗一般的笔墨描绘了陈子沐的乡村农家生活,以及农家子弟充满田园情趣的劳作、游戏、爱情生活,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
乡绅精神表现在陈子沐身上,也是他急公好义,不畏强权,为民请愿,带领乡民反抗苛税、为弱者伸张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小说第三十一章写刚从长沙府学求学回乡的陈子沐,一路看见蝗虫遍野,农人颗粒无收,却还要上交繁重的赋税,心急如焚,不惜冒杀头危险提笔写下《上皇帝书》,秉实直言,终使茶陵州民减轻赋税,人民因此勒石纪念。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写陈子沐为未能及时完税而遭到恶吏毒打的老实农民陈树兰撑腰解难,却被恶吏刘礼忠罗织“把持钱粮、抗缴国科”的罪名报复,最后惨遭杀戮。
福柯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应该属于真正的“社会分子”,永远对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和一切的社会现象保持批判。这种批判一定会有切实的理由,而斗争的胜利一定会改善某些人的状况,改变某种权力关系,不是为了某种虚无缥缈或不切实际的目标,更不会用一种压迫取代另一种压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乡绅,首先应该是乡村知识分子。乡绅精神,除了传承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传统的道德内核,更应该有一种敢于独立于官府之外的“在野”气质,一种敢于舍生取义的责任担当。这种勇气和担当,使得自明以降几百年来,乡绅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精神脊梁。
苏洣云的长篇历史小说《子沐大人》,无疑对中国传统乡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新的典型,更对久已失魂的乡绅精神发出了深情而痛楚的召唤。面对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呈现的文化荒漠,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人物进行创作,寄寓了自己深沉的审美理想。
从《子沐大人》一书可看出,作者遵循其真实性的审美原则,采集了大量的史料,对人物和史实做了翔实的考据。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诗文、碑铭、传记、甚至是摄影图片,无不体现高度的历史真实。
但作者也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写成单纯的人物传记,而是充分发挥了艺术创造,人物塑造得较为丰满立体。小说中还充满大量的民俗、童谣、民间戏曲、民间传说的叙写,甚而不避讳带有传奇和演义色彩的情节,正文之外又加闲笔,细节丰富真实,节奏从容不迫,舒卷自如,加之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其民间性和趣味性使人读起来颇感兴味。
为乡绅精神招魂——读《子沐大人》
王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