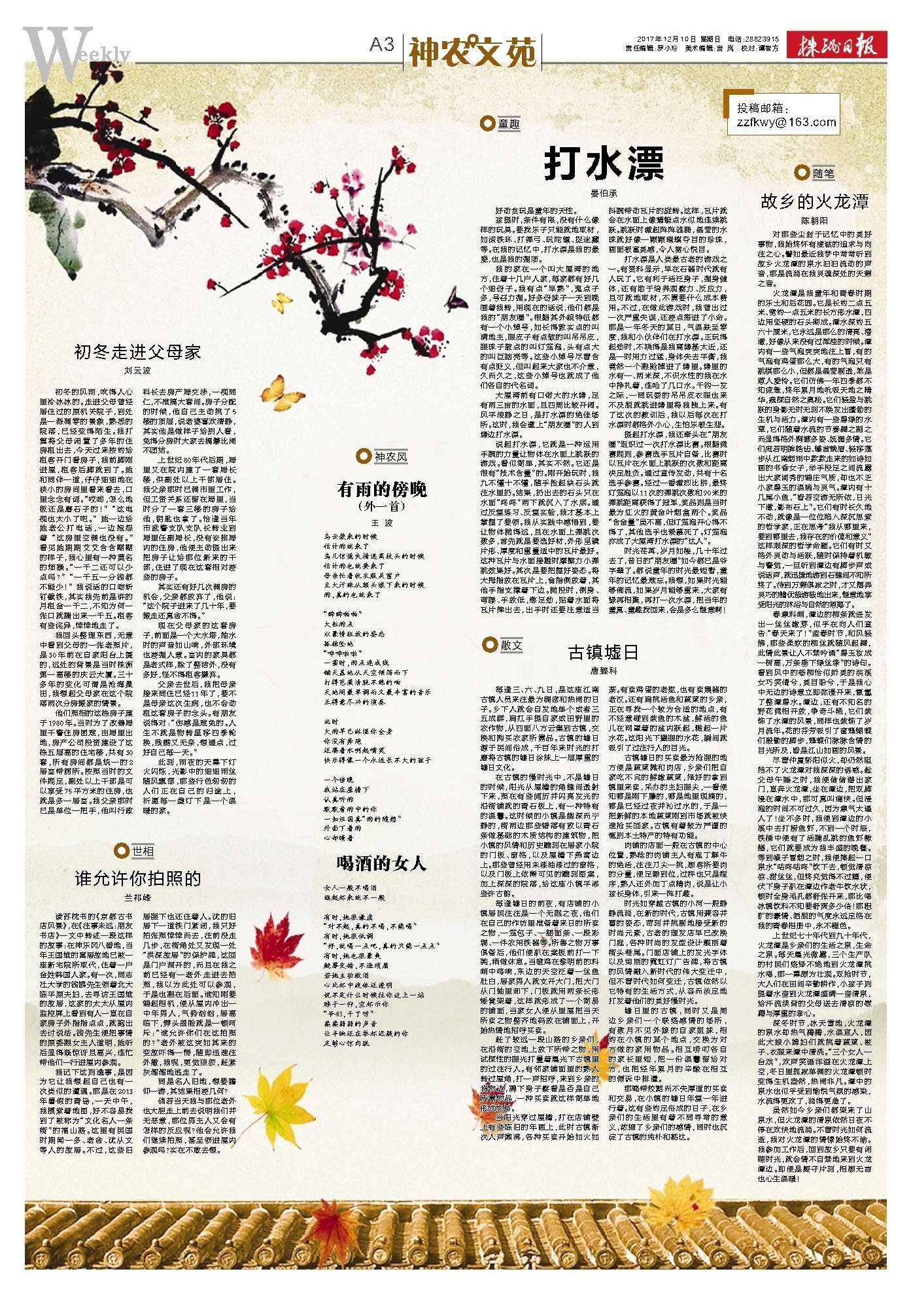古镇墟日
每逢三、六、九日,是这座江南古镇人员来往最为稠密和热闹的日子。乡下人就会自发地单个或者三五成群,肩扛手提自家或田野里的农作物,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古镇,交换和购买农家所需品。古镇的墟日源于民间俗成,千百年来时光的打磨将古镇的墟日涂抹上一层厚重的墟日文化。
在古镇的慢时光中,不是墟日的时候,阳光从屋檐的角缝间透射下来,照在有些阅历并闪亮发光的沿街铺就的青石板上,有一种特有的温馨。这时候的小镇是幽深而宁静的,街两边那些错落有致以青石条做基础的木质结构的建筑物,把小镇的风情和历史雕刻在居家小院的门板、窗格,以及屋檐下燕窝边上。那些曾经用朱漆油漆过的窗格,以及门板上依稀可见的雕刻图案,加上深深的院落,给这座小镇平添些许古韵。
每逢墟日的前夜,有店铺的小镇居民往往是一个无眠之夜,他们在自己的作坊里准备着来日的所卖之物,一笼包子、一捆面条、一段彩绸、一件农用铁器等。所售之物万事俱备后,他们便趴在案板前打一下盹,稍做休息。当雄鸡在黎明前的料峭中鸣响,东边的天空泛着一丝鱼肚白,居家男人就支开大门,把大门从门轴里卸下,门板就用两条长形矮凳架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易的铺面,当家女人便从里屋把当天所卖之物整齐地码放在铺面上,开始热情地招呼买卖。
赶了较远一段山路的乡亲们,在沿街的空地上放下所带之物,用试探性的眼光打量着晨光下古镇里的过往行人。有邻家铺面里的熟人转过屋角,打一声招呼,来到乡亲的货物边,蹲下身子察看是否是自己所需物品,一种买卖就这样简单地形成交易。
当阳光穿过屋檐,打在店铺壁上有些陈旧的年画上,此时古镇渐次人声鼎沸,各种买卖开始如火如荼。有卖鸡蛋的老妪,也有卖篾器的老汉。还有肩挑活鱼和蔬菜的乡亲,正在寻找一个较为合适的地点,有不经意碰到装鱼的木盆,鲜活的鱼儿在网罩着的盆内跃起,溅起一片水花。这阳光下耀眼的水花,瞬间就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
古镇墟日的买卖最为抢眼的地方便是蔬菜摊和肉店,乡亲们把自家吃不完的鲜嫩蔬菜,择好的拿到镇里来卖,采办的主妇眼尖,一看便知哪是刚下藤的,哪是地里现摘的,哪是已经过夜并沁过水的,于是一把新鲜的本地蔬菜刚到市场就被快速抢买回家。古镇有着较为严谨的甄别本土特产的特有功能。
肉铺的店面一般在古镇的中心位置,熟稔的肉铺主人有庖丁解牛的绝活,往往刀尖一挑,顾客所要肉的分量,便足额到位,过秤也只是程序,熟人还外加丁点精肉,说是让小孩长身体,引来一阵打趣。
时光如穿越古镇的小河一般静静流淌,在新的时代,古镇用兼容并蓄的姿态,苛刻并挑剔地接受新的时尚元素,古老的理发店早已改换门庭,各种时尚的发型设计靓丽着街头巷尾。门面店铺上的发光字体以及绚丽的霓虹灯广告牌,将古镇的风情融入新时代的伟大变迁中,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依然以它特有的生活方式,从容而淡定地打发着他们的美好慢时光。
墟日里的古镇,同时又是周边乡亲们一个联络感情的场所,有数月不见外嫁的自家姐妹,相约在小镇的某个地点,交换为对方做的家用物品。相互唠叨各自的家长里短,把一份温馨留给对方,也把经年累月的辛酸在相互的倾诉中排遣。
那略带狡黠而不失厚道的买卖和交易,在小镇的墟日年复一年进行着。这有些约定俗成的日子,在乡亲们的生活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浓缩了乡亲们的感情,同时也沉淀了古镇的纯朴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