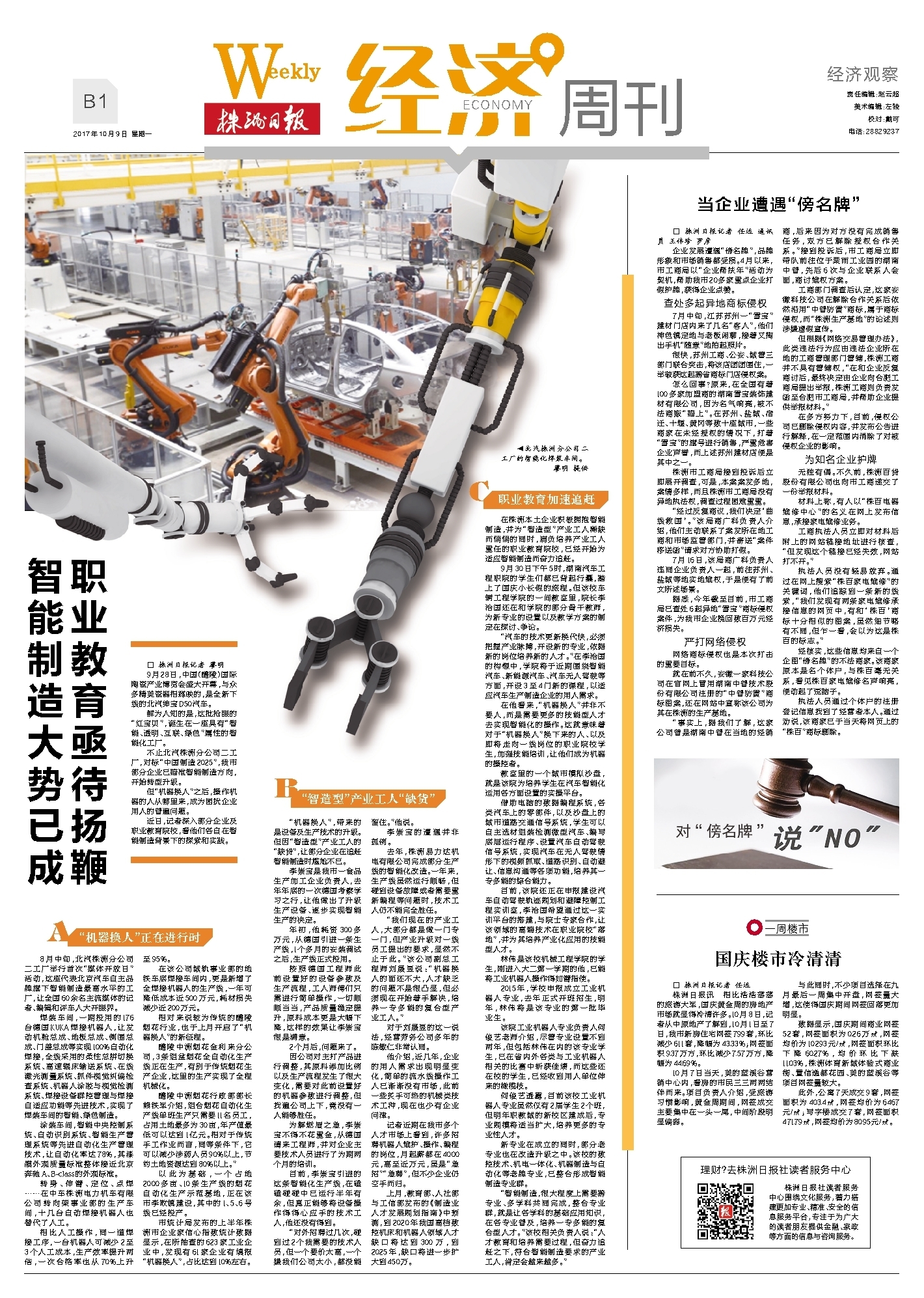报社给我四个第一次
征文选登
袁楚湘
傅泽斌
岁月,如流水一样过去。60年了,我与《株洲日报》的情结,点点滴滴,难以忘怀。
1957年,正在二中读高中的我,写稿兴趣特浓,一篇篇文章投寄长沙、湘潭。10月2日那天,我到市文化馆看书报,突然眼睛一亮:《株洲日报》创刊号!顿时,我欣喜若狂。第二天,我就为它写稿了。接连发表了几篇稿子后,不久,我接到报社通讯员聘书,成为报社第一批通讯员。
我经常到报社去送稿和反映情况,与报社领导和编辑记者们联系密切。在学校大搞生产劳动修百草冲水库时,我们日夜战斗在工地,《株洲日报》为此开辟了一个专栏,记者王家元到工地采访,首先就找到了我,指导我写了好几篇通讯报道。我们成了密友。如今王老已90多岁,我们还互致问候祝福不断。报社社长王又民同志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得知我们二中学生成立了白杨文学社,立即将他在《株洲日报》发表的几首诗歌的6元稿费寄给我们作办刊经费,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们。那时《株洲日报》在全市只发行了1000多份,我们白杨就订了两份。由于我宣传党报和写稿积极,《株洲日报》第一次评优秀通讯员,我有幸名列其中,名单刊登在群工组编的通讯刊物上。
1964年,《株洲日报》和市文联联合举办《日月换新天》征文活动。6月的一天,报社记者沈良桂老师到三中采访,我给他介绍了学生何开明帮助盲人周桃仙学笛子、学文化、学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沈记者觉得这个题材很好,建议我写篇文章参与征文活动。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写了《短笛一支颂新风》刊登在7月6日《株洲日报》上。后来,这篇文章评为优秀奖(那次征文未分等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的文学创作奖励。
1975年,我从株洲县借调到《株洲日报》农财组助勤。2月,市里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前,组长黄文带着我到株洲县农村采访;会中,黄老师又带着我和从二中借调来的陈辉老师搞会议报道,一天一个版面。我们报道组三人住在钟鼓岭利民旅社(原市公安局对面),白天参加会议、采访,晚上写稿,第二天见报,忙得不亦乐乎。黄组长和我虽都住在附近操坪,但晚上都不回家。会议闭幕前一天,黄文老师对我说:“小袁,会议明天闭幕,要发个社论,你先起个草吧。”我写过通讯报道,也写过诗歌散文,就是没写过社论。组长交代的任务,我不好推辞,只好试试。一天一晚,我写了一篇《实现农业新跃进——热烈祝贺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胜利闭幕》的草稿,三个人一讨论,觉得尚可,集思广益修改了一下,第二天见报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学写社论,机会是报社给的。
1984年7月,报社副刊部编辑黄俊老师找到我,说:“文化革命后,书店很少有文学方面的书籍。我们很多读者想学学文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准备开辟一个《作家小史》专栏,你是文革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能不能任这个专栏的主笔?”我欣然答应试试。7月22日,第一篇《屈原》见报了。以后每期副刊一篇,从春秋战国一直写到明清,系统简练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作家作品。据说,当时有不少读者将这些文章剪报下来,以备查阅。这是我在报纸上开辟的第一个个人专栏,机会又是《株洲日报》给的。
从创刊到现在,《株洲日报》陪伴我度过了整整60个春秋。如今,我私费订了《株洲日报》和《株洲晚报》,坚持天天读报,有时还为它写写稿。我深深感到,在我的生活里,一天都不能没有它。
“傅伯伯,又去看报啰!”一出门,邻居就打趣我道。每周的一、三、五是邮政投递员送报的日子,也是我去看报的日子。我的这一举动,沿途群众习以为常,“又去看报”成了我和乡邻之间的口头禅。当然,背后也有人议论:“七十多岁的人了,不晓得去打牌,天天只晓得去翻了这几张报纸,真有点哈(傻)气。”
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到离家不远的长岭社区或长岭新街居委会看报,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自觉行为和心理需求。如果这天因事没看报,第二天我就一定要补看,不然吃饭也觉得不香、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假如哪天未看到《株洲日报》,我会记上日期,到其他地方或单位寻找补看。我对报纸之所以这么情有独钟,一切缘于《株洲日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株洲日报》社的编辑兼记者覃冬清来到当时的株洲县长岭公社采访致富带头人——一名靠烧红砖、种水稻和经济作物年收入超万元的社员傅长根。公社领导带覃记者来到了我家,让我协助他进行采访。和覃记者一起现场具体了解了傅长根的事迹后,覃记者吩咐我写个材料寄给他。后来我撰写的材料在覃记者的修改指正后,《万元户傅长根》不久就见报了,株洲县广播电台也将文章内容播放了多次(当时广播是城乡宣传的主要媒体)。傅长根成了当地一名致富典型,后来他还作为长岭公社的代表,出席了株洲县政府举办的致富典型表彰大会。
从此,在覃记者的指导下,当地有什么典型事例我就会及时写好寄给报社,进行宣传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写了一篇关于长岭肉食站职工曾立下岗后在家养猪致富的报道,材料见报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株洲县广播电台多次进行了转播,曾立一下子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再就业典型,来他家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我也成了名符其实的《株洲日报》通讯员,更加体会到了写好宣传报道稿件的价值,写稿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对《株洲日报》的感情也更加浓厚,每天看报也成了我的一种享受和追求!
2014年,我从《株洲日报》上看到市档案局开展家训家规的征集活动后,积极响应,撰文投稿。所有参与者写的材料内容通过政府网络公众投票后,我获得了全市三等奖。《株洲日报》记者成建梅对我写的主要内容,作为市文明家风进行了专题报道,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我坚持看书看报的积极性。
我看报纸,对有的内容看一遍,有的内容看两遍、三遍,看后再将重点内容归类整理收藏,如分为政治时事、文学写作、养生保健、历史名人等。书报是我家的收藏珍品,也是我的终身伴侣,活到老学到老是我老年生活的主旋律,报纸上的见闻也是我与人交流的主要话题。《株洲日报》丰富了我的生活,增长了我的见识,是我进步的引路人、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报社原编辑罗仲威、王显谈、廖明等记者都是我的好老师,我衷心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
结缘
张秋华
“结缘”本是佛教语。季羡林先生曾经对这种“机缘”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报纸上的词儿是“机遇”,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命运”。谈到《株洲日报》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掂量来掂量去觉得似乎“结缘”二字形容最为妥帖。
粗略掐指一算,我与《株洲日报》结缘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时间回溯到1993年的暑假,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株洲日报》举办的“大地”文学通讯员讲习班。参加那次培训的学员大多为国有企业宣传干部或行政事业单位文字工作人员,如今好多早已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因为那次“机缘”,我才渐渐地跟《株洲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报社之间的人际交往颇有雅儒况味,大家常常以“老师”称谓长者、智者或尊者。精彩的讲课恍如昨日历历在目,至今犹觉受益匪浅。姚天元老师列举的抨击“官本位”泛滥的时评文章《和尚就是和尚》,回想起来忍俊不禁。颜青春老师援引身边的人和事教授新闻写作,称得上是自己新闻宣传路上的真正“启蒙老师”,我的新闻处女作《爱心,在这里闪光》便是在其直接指导下才得以发表在《株洲日报》“星期天专刊”。刘醒波老师用红笔一页一页不厌其烦修改通讯员的习作,字里行间浸润着编辑记者的艰辛和对写作者的关爱……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深切地感知学艺拜师的极端重要性。在《株洲日报》许多见过面和未曾谋面的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一年下来总有些“豆腐块”文章见诸报端,熟识的人亲切地称自己“土记者”。
人生有时就是那么神奇,偶然性的链条会彻底改写生命的轨迹。1997年,通过县里组织的文秘人员遴选考试,我不经意间从教育部门跨入宣传行当。说起其中缘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株洲日报》发表的大大小小文稿。这以后,我和《株洲日报》之结缘更为紧密,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读报纸(这是上班的第一堂课,相当于学生时代的早读)、写报纸(当时报纸上来自基层的新闻稿,大多出自通讯员之手)、卖报纸(征订党报党刊是宣传部门一件大事,有时还要磨点嘴皮子)构成了日常工作经久不衰的“三部曲”,与《株洲日报》的关系可以说得上形影不离了。
平台,就是人生实现梦想的舞台。我深深地觉得,所处发展平台不佳,无异于身陷“沼泽地”进退维谷,若非超强意志者只能逐渐“老”去徒然销蚀生命。幸运的是,我成长路上曾经结缘《株洲日报》这个大好平台。“脚底下出新闻”。从事新闻宣传的那段日子,我走遍了工作所在县里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耳闻目睹的人和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更加真切地感知了农村的美好和无奈。“宣传无小事”,经年累月和《株洲日报》等党报党刊打交道,潜移默化中得到各方面的历练和进步,担当和责任深深植根骨子里。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02年7月18日在《株洲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铺就希望路》的通讯报道,不知哪个环节出现差错,见报时误把“人平获利500元”变成了“人平获利500万元”。“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读者看到了还会以为大跃进“放卫星”的浮夸风又回来了。提前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把全县5000多份《株洲日报》截留下来,用墨笔一份报纸一份报纸地涂掉这个可恶的“万”字。在我的感染下,邮政工作人员也一同帮忙涂抹报纸。结果,这份报纸传到县里,不仅没有人怪罪,反而对这篇报道好评如潮。
《株洲日报》故事多,类似的“糗事”或啼笑皆非的事情举不胜举。近七八年来,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的变迁,我与《株洲日报》“零距离”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每天坚持阅读《株洲日报》等党报党刊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与《株洲日报》结缘的那种浓郁的情愫一直没有淡化。
《株洲日报》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我无怨无悔与《株洲日报》之结缘!
成长
管弦
认识《株洲日报》的时候,我还很小。
那时,报社在市中心。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建有一个花园,圆圆大大的,好像一口大铁锅,人们就把它叫做“大锅饭”。大锅饭的东边连着红卫桥,红卫桥后来改名为新华桥。我常常从我家所在地——当时很红火的601厂出发,经过红卫桥,绕过大锅饭,去报社投稿。
那时的投稿,真的是投上稿子。自己的文章一律是手写打好草稿后,再用方格稿纸誊写,放进信封里,寄送到编辑老师手中。那方格纸上的字,是一律用吸着碳素或蓝黑墨水的钢笔写好的,标点符号也占用一个方格,规矩而漂亮。我喜欢这样的书写,有时写上正楷,有时写上行书,有时写上仿宋,有时写上魏碑,有时写上小篆。手指和笔尖轻轻在纸上滑动着,字儿和纸儿便慢慢融为一体,安静、坦然、从容,宛若一件仙气飘飘的艺术品,透着清清长长的芬芳。
我常常虔诚地写着这些文字,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落在他人心中,长成一棵苍翠挺拔的大树。株洲日报社的每一位老师,就给予了我这样的信任和鼓励。每次,我握着自己的文章,从位于大锅饭旁边的市一医院后门外的楼道口、踏入位于二楼的报社、向编辑老师投上自己的稿件时,都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会受欢迎。庆幸的是,每次,我都能看到老师们亲切的笑脸,听到他们热情的话语。他们微笑着鼓励我,多读、多写。特别是第一次投稿的文章《等待》很快就发表出来后,我看到了一种叫做激励的东西。
《等待》,是我在《株洲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书写的是一种少年的情怀。我还没有看见刊发了这篇文章的报纸的时候,很多亲朋好友就看见了,纷纷打我家座机电话,说着表扬的话。有几个同学还说要我请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在傍晚时分来到了我的位于郊区的学校。我只好张罗晚饭,郊区偏僻没有饭店,我便去食堂买来饭菜,用铝制方型饭盒、铁制饭盆、搪瓷碗等餐具盛着,又去小卖部买来葵花子、花生、小花片、水蜜桃汁这些当时很流行的零食和饮料。同学们拿着不锈钢勺子,快快乐乐地吃着喝着。欢乐的清脆的稚气的声音,把晚霞映衬得格外鲜艳。席间都问到稿费,得知有6元,便都有些不好意思,对我说,那你今天请客就花费了好几个6元了。
现在想来,那时的人,真是很爱学习的,他们会征订和购买各类报纸、杂志、书籍,并认真地阅读,看到相熟之人的文章,他们还会奔走相告,谈论自己的看法。《株洲日报》,更是他们每天必读的。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已经围绕《等待》谈了很久了,觉得要下次再谈了。他们走到传达室旁边的自行车停放处,跨上26或28的自行车,回头对我笑着挥手。我站在宿舍楼三楼的走廊上,我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如新鲜牛奶般倾泻而下的月光中,竟然是黑灰黑灰的。我想了想,应该是吃了葵花子的缘故吧,那小卖部卖的现炒葵花子,一直就多灰且黑。我忍了忍,没有笑出声来。回到宿舍照镜子,我的嘴巴也沾了黑灰色。
后来,大锅饭拆了,和大锅饭相连的西边的桥建起来了,河西变得越来越美。株洲日报社搬迁到河西。《株洲晚报》也诞生了,和《株洲日报》一样生机盎然。我参加了省里第一批电脑操作培训班,学会了用五笔字型打字。再去投稿时,除了投手写体,也会投打印体。那时,《株洲日报》发表作者文章时,要由编辑老师填写发文签单,连同稿件一起,交到打字室去打印,然后排版发表。编辑老师常常很快看完我的稿子,当即表示会发,要我直接送到打字室打印,还直接给我一些发文签单,要我自己填好,投稿时一并送来。这样的温暖,让我充满感激。在感恩中,我告诫自己,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陷害和打击,都不要害怕,要依然满怀善意地奋勇前行。
《等待》过后,一直至今,我投往《株洲日报》的每一篇文章,都得到了发表,悠然地长成了树。在这些树儿面前,我深深记住了株洲日报社的每一位老师,他们都像辛勤的园丁,无私地为我的树儿浇水施肥,并我和一起,看着树儿成长。
岁月如金,绚美且长。流彩的光阴里,我看到一种叫做坚持的东西,和《株洲日报》一样,闪耀着隽永的光芒。
《株洲日报》,让我们一起加油。
你是我最温馨的回忆
黄玫
从空间看到文友的一篇文章,得知《株洲日报》成立60周年,顿觉有一根仙人的手指触动我心中最想呵护的地方——《株洲日报》,我曾经的美丽时光!
初识《株洲日报》时,我还是个12岁的小女孩。当年我家住在株洲县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母亲是小学唯一的公办老师,放学后,我就坐在办公室母亲的办公桌上浏览《株洲日报》。真正意义上读《株洲日报》是在初中时期,记忆里那个暑假,《株洲日报》每天都有小说连载“一双绣花鞋”“梅花牌手表”等。每次读完连载,就盼明天快到来,等待的日子难熬又漫长,第二天一清早,我就会坐在学校的大门口眼巴巴地盯着大路,期盼着邮递员出现。每天都是我接过邮递员的报纸,在那个年代,是《株洲日报》陪伴我度过了落寞的青春期。
后来,我参加工作在田心铁路商店上班,城里的灯红酒绿与曾经带过的穷乡僻壤成了鲜明的反差,我的淳朴含蓄与城里人的开放与时尚总是相距甚远。于是,业余时间,当室友去舞厅跳迪斯科或约会男朋友去了,我就一人在寝室读名著,写诗读诗。1986年5月8日,我的现代诗“芬芳的花瓣”第一次发表在《株洲日报》!在散发着油墨香的《株洲日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兴奋又激动,我那多年封闭自卑的性格豁然开朗,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成功与满足感。一个星期后,我收到《株洲日报》信封装着的稿酬领取通知单,觉得自己是一个文人了。第二天,我来到株洲日报社传达室,递出稿酬单,说:我来领稿费。清晰地记得,接过传达室给我的稿费,一看5元,多了一元,我又返回,退回1元,说:多给了1元。领了4元稿费,我买了一筒面条,在寝室的走廊用煤油灯煮面条,剩下的钱吃米粉。一个月的工资每个月除了买书,常常是月光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化工单位。已是人妻人母的我人生三点线:上班 ,家庭,菜市场。我值零点班的时候,面对夜深人静,就摊开稿纸写文章写诗,军大衣口袋里装着一大沓稿纸。1994年,我再次投稿《株洲日报》,文章“我下岗休息”轰动全厂。
1998年,《株洲日报》星期天专刊有一段时期,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的豆腐块,如“徐家桥小巷”、“你让我好失望”、“小偷扒掉了我的孝心”、“母亲亲手做的腌菜蒸肉”等。厂里各科室车间都抢着看《株洲日报》星期天专刊,我被称为“一支笔”。那年,我收到丁文浩老师的一封亲笔信,说我文笔较为流畅,是女作者中较为勤奋的一个,还指出我的不足,要开拓题材的意思,丁文浩老师字迹洒脱如行云流水,温暖了我茫然探索的心,也坚定了我热爱文学的意志。这封信珍藏了几年,直到家庭发生变故,被赌博的丈夫把我所有的书籍连成那封信都卖到废品店去了,让我遗憾多年。
2003年单位破产,婚姻也随着解体。2008年孤身来到长沙打工,每天迎着朝阳出门踏月回家,用6年打工的积蓄在南门口开了一个玉器店。辍笔13年再回到文学圈时,我发现自己成了原始人,报刊早已经不接受信封投稿,而我却不知道电脑投稿,就连电脑打字也是读大学的儿子教的。在一个文友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电脑投稿。散文“有一条小狗叫白丹丹”发表在2015年4月29日《株洲日报》,是万宁老师告诉我的邮箱。我兴奋地告诉母亲,大姐找到《株洲日报》在电话里读给母亲听,后来,大姐告诉我,母亲在电话另一头大哭。2016年2月在《株洲日报》发表一篇元宵节的文章,收到50元稿费。
从一个12岁的花样少女到半百,不管是贫瘠的过去,还是物质繁华的今天,《株洲日报》渗透在我的岁月里,给了我最温馨的回忆!